
标题

标题
内容
余 丛 | 吾心安处是故乡
更新时间:2024-09-05 作者:余 丛来源:广东作家网
在遥远的鄂西大山里,有一座不起眼的村庄叫鲍坪。虽然我从没有去过鲍坪,但是我仍然通过朋友谭功才的文字想象过鲍坪,乃至认识了鲍坪,这里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成长的故土。直到有一天,不安于现状的谭功才,为了谋生和发展,远离了他的家乡,来到遥远的南方沿海城市,并在异乡成家立业。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谭功才用三十年的时间,矢志不渝地为鲍坪树碑立传,写出了两部重要的散文作品集,一部叫《鲍坪》,另一部叫《鲍坪记》。从走出家园鲍坪,到回到书本上的“鲍坪”,或许功才作为作家的要义,就是为了完成某种著述的使命,现在也该放松一口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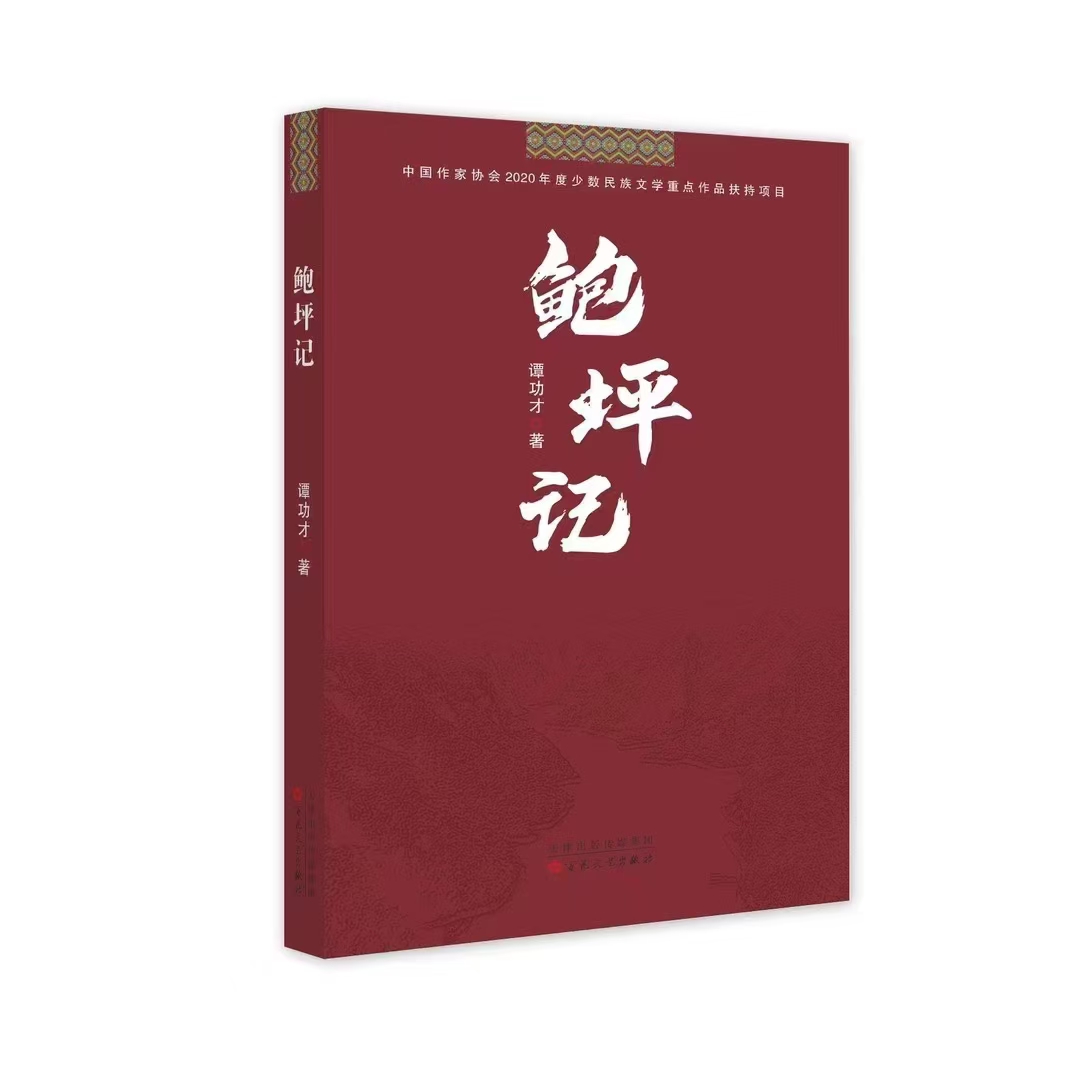
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辈人,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或多或少会有一段乡村印迹,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不尽相同的“鲍坪”。只不过谭功才把它诚恳地记录下来,而我们却逐渐将自己的村庄从记忆中抹去,没有了祖辈的乡村也只能随之消逝。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疯狂吞噬,更多的乡村必将沦陷于时代的推土机。显然,谭功才的书写是弥足珍贵的,不管是对故乡风物的遐想与咏叹,还是山居人情的思念与追怀,他无形中写出了一代人的乡愁。然而,这样的乡愁又能有几分美好可言?功才笔下娓娓道来的“鲍坪”景象,处处饱含人世的辛酸和苦难,又弥漫着蹉跎岁月的感伤和悲情。而今,能够共情的同代人已经日渐衰老,被连根拔起的后辈也只能面带惊讶的神情,又如何能理解或审视“鲍坪记”里的生存困境。
有个譬喻很形象,艺术是患病的贝壳生出的珍珠,而乡愁好比游子的怀乡病。在世俗意义上,故乡是回不去的他乡,只有远离了才拥有美好的印象和记忆,走近了却又生出胆怯之心。白居易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也许途中方是游子的心安之地,异乡才是漂泊者落脚的处所,而故土只是被反复回望的风景,因此,“乡愁”对谭功才而言不是浪漫的意境,也非一劳永逸的治愈,而是遣怀疗伤的一剂药方:再“巴掌大”的地方也有一方天地,再闭塞的山窝也有一条出路,再古老的村落也有无数盼头。正如他所言:“只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才使得我能够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烛照下,重新审视和回望乡土意义上的鲍坪,使之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永恒。”
从《鲍坪》到《鲍坪记》,后者是前者的续篇,是谭功才对故土的意犹未尽。它们一脉相承,又互为映照,一事一物取材于作家过往的乡村生活,一情一景受益于滋养他的那方水土。然而,字里行间隐现的愧疚、无奈和真情,乃至鲍坪人的血与泪,不正是中国山村社会的缩影吗?假以时日,《鲍坪》二书的价值会越发凸显,将是一部描写鄂西山村风土人情的重要著作,或人文风物,或地理风情,或世事伦常,堪比“乡村志”式的百科全书。当然,这得归功于功才的散文与他的为人一样诚恳,不炫弄不花哨,不做作不张扬。既有切身体验,又有客观语境,读起来平白生动,亲切感人,更有一种诗性的沉思。这样本真而清峻的散文,恰恰在当下喧嚣的文学现场显得稀有,同时,作家通过文字对原产地鲍坪的重新定义,构建了自我心灵上的归宿。
人生如云驻,故土亦不过是生命的驿站。《鲍坪》和《鲍坪记》二书,宛如谭功才的一曲哀叹的“呼愁”,也将是我们朋友的眼中,乡村文明的最后挽歌。随着城愁时代的来临,精神上的返乡和寻根,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法辨识,而数字化的未来,必然定义虚拟空间的“乡愁”。然而,每一种“乡愁”都是深情的遗憾,在被思维和算法驾驭的非物世界,“乡愁”也将被数据肢解为碎片化的情态。总之,每个人都身处历史的大潮,被洪流裹挟或淹没,只有强者捆绑着石头浮出水面。当数字化秩序接替了大地的秩序,即使来自鲍坪的谭功才,终归无法逃脱苏东坡那句至理箴言: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