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莫华杰 周聪 | 我不是一个冲动的写作者
更新时间:2023-08-25 作者:莫华杰 周 聪来源:文艺报

莫华杰,一九八四年生于广西钟山,现居广东东莞。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花城》《作家》《山花》《天涯》《芙蓉》等文学刊物。小说集《赊佛》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著有长篇小说《春潮》、长篇纪实文学《世界微尘里》。曾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广东有为文学散文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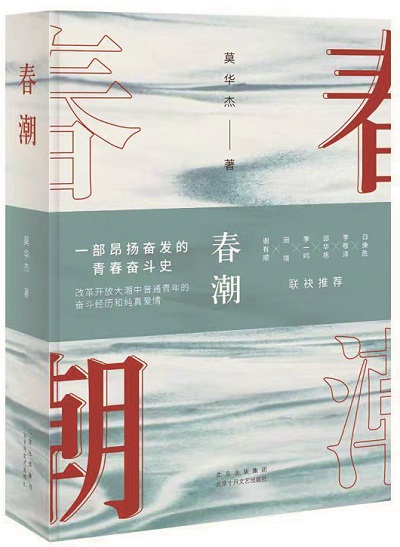
讲好身边每一个故事,希望能感染到每一个读者
周聪:华杰好,我想先从五月你刚获得漓江文学奖的作品《世界微尘里》展开今天的对谈,此书原名《我的打工生涯》,后来才以李商隐的五言律诗《北青萝》中的句子命名,十几年的打工经历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体,工厂经验于你而言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李蔚超在《你的生活何以成为传奇?——莫华杰论》一文中首先从身份认同和文学谱系学两个层面进行了辨析,并将你的作品冠以“新工人文学”的标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打工经历对你的创作风格有何影响?或者换一种说法,你是如何看待“打工文学”“新工人文学”这一类的命名?
莫华杰:周聪好。现在很多人对打工这个词颇有贬义,认为打工是卑微的代名词,打工仔没什么技术和文化,依靠体力劳动赚取低微收入。后来官方为了避免歧视,将其重新命名,最初改为“新的产业工人”,后来索性改为“劳动者”:不管你在工厂还是国企,还是在政府单位,大家都是劳动者,没有贵贱之分。《世界微尘里》获得的第一个奖项,就是202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榜”。我从不避讳别人说我是打工仔,也不避讳别人说我写打工文学。
在我心中,“打工”这个词是很神圣的,也充满温馨。上世纪90年代末,打工就跟上大学一样光宗耀祖,谁家里要是有人在外打工,寄钱回来,这个人便挺直腰杆走在村里,狗都不敢朝他叫。我那时格外向往打工,渴望通过打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我心目中,没有比打工更能安放我的命运了。正因如此,当别人说我是“打工作家”,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文学嘛,只要写得好,让读者喜欢,叫什么都无所谓;写得不好,说你写的是“皇帝文学”也没用。
言归正传。打工经历带给我丰富的人生体验,获得了很多别人没有的一手故事。如同厨师做菜,食材越丰富,发挥的空间就越大,哪怕是刚出道的厨师,炒十道菜,总有几道端得上桌。我的创作风格“讲好身边每一个故事,希望能感染到每一个读者”,就是在这种生活体验中逐步形成的。

周聪:《在执迷不悟中觉醒》是一篇很真诚的创作谈,我注意到,“故事”是一个高频词,它构成了你的一种创作“方法论”,这也许与你的阅读经验相关,《世界微尘里》中放牛时读金庸、古龙等通俗小说的儿时经历也令人印象深刻,《春潮》中空置的话梅坊的墙壁上贴着金庸电视剧的海报,以及这篇创作谈中对金庸“雅俗共赏”的推崇,都可以佐证你对金庸作品的喜爱,顺着这个话题,具体到小说的创作,从故事到文学作品之间的转换,你有哪些经验?
莫华杰:刚开始写作,没有什么经验,我都是按照“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个套路,老老实实讲故事。先把故事讲好,吸引人,再慢慢思考文学性。就像一个初学打羽毛球的人,首先要学会发球、接球,熟练之后才学扣杀、吊球、放网等技巧。哪怕是世界冠军,都得从最基本的入门开始,基本功不扎实就学技巧,容易走偏门,一旦形成肌肉记忆(惯性),就很难纠正过来。
文学也一样,如果一个人连故事都讲不好,就开始卖弄技巧,写出来的东西很容易飘。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故事和人物都非常扎实,开场大多也都是“从前有座山”。我深受影响,写小说第一原则就是把故事讲好。有故事,就有人物,能吸引读者,可以成为三流的文学作品;再把人物往深处写,加入生活细节,挖掘内在的人性,这就有了一定的文学性,可以成为二流作品;文学其实就是语言的艺术,人物和故事都有了,人性也出来了,若是文字再打磨出光芒,那就是一流的作品了。
只要掌握这三个法门,循序渐进,时日一长,多少有些长进。当然,有些人天赋好,故事和人物、语言同时修炼,几篇下来就显示出卓越才华。我没有这样的才气,从最初的讲故事,到现在学习打磨文字,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春潮》一口气写了40万字,人物和故事很扎实,得益于这么多年的笨功夫。《世界微尘里》写的是自己的故事,只有十几万字,按理说几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我足足写了五年,因为我用生命去打磨每一个字,希望能赋予它们温度。
周聪:熟悉你的读者都知道,你11岁发现有强直性脊柱炎,疾病带来的疼痛与吃药之苦只有你深知其中滋味。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也说过:“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鲁迅曾做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讨论药和酒与魏晋时代文风的关联。在《世界微尘里》,我可以看到你对买药和治病不厌其烦的书写,《春潮》中罗祥兴给癞蛤蟆打针的恶作剧、刘见章对欧阳源的长期针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疾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的表达,它造就了一种与他人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方式。我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疾病与自己创作的关系?
莫华杰:11岁那年我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小学毕业后无法读初中,只好辍学在家务农。《世界微尘里》第一章就写我如何与病痛作斗争,吃了各种离奇古怪的药。而那时,我正迷恋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宗教等知识。因患病原因,我对医学知识特别感兴趣,金庸的小说为我构建出一个奇妙的中医世界,我在治病的时候也时常突发奇想,甚至自己时常跑出去挖草药,回去熬汤汁,幻想能治好体内的病。写长篇《春潮》,我便将这些想法融入其中。
强直性脊柱炎是治不好的,我现在经常腰骨僵硬,发胀发痛,由于长年吃药,身体弱不禁风。尽管我很痛恨这个病,但没办法,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无法改变。当然,因为这个病我才走向写作这条路,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相辅相成,没有人能过完美的一生,把不完美的东西写到文学作品里,也算是创作的另一条道路吧。
周聪:《南瓜》《赊佛》是两篇我挺喜欢的作品,在读这两个短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朱山坡的小说集《十三个父亲》和田耳的短篇小说《衣钵》。《南瓜》塑造了一个意外丧子后的父亲形象,他一系列略显疯癫的行为敞开了一个父亲内心深处巨大的痛苦,在邻居们的合谋“反击”与儿子的暴击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坍塌了,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赊佛》中的父亲是一个恪守乡村丧葬伦理的佛佬,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民间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都是这篇小说探讨的命题。在当代文学史中,父亲的形象谱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我们如何书写父亲?或者说,我们如何复原父亲作为普通人的民间性的一面?请你结合自己的创作谈一谈。
莫华杰:《南瓜》应该是我第一篇纯文学处女作。我十六岁那年开始萌生写作的想法,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外出打工,在打火机厂、家具厂、电子厂当员工,也在饭店做过服务员。虽然生活漂泊,但我仍坚持写作,到了2006年,生活固定下来,我开始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作品。当时写的都是通俗文学,2011年,东莞长安举办改稿会,我才开始学习写纯文学。
《南瓜》的灵感,来自于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当时我读到这篇小说,虽然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但是文中父亲的离奇古怪做法,却让我大受震惊——故事竟然可以这样写,人物居然可以这么设计。于是灵感来了,我便一口气写下了《南瓜》。如今,我写了几十个中短篇,不知道为什么,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南瓜》。
《赊佛》故事源于生活,写起来也很顺手。我家是风水世家,从太爷到大爷,再到我父亲,现在传承到我弟弟身上,这也算是民间风俗传承吧。我到广东打工,曾在工厂做了五年的业务,对打工生活极为熟悉。《赊佛》讲一个乡村师公佬(道士),为了不让祖传的《赊佛经》失传,跑到东莞找他的独生子,要利用儿子业余时间教他学会佛经。儿子是个业务员,整天跟客户打交道,在花花世界中迷失本性,哪里可能愿意学这些东西。这是信仰的冲突,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最后只能通过死亡,来提醒当下这代人对民间信仰的重视。
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一直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思考的命题
周聪:《春潮》也被誉为“一部昂扬奋发的青春奋斗史”,这部洋洋洒洒四十万言的作品采取了情感线和创业线并进的叙事策略。先来看情感线:冯源与欧阳娴之间的情感碰撞,从误解、接纳到人为分开的错位之爱,冯源的心理嬗变被精准地呈现出来;同样,陈嘉南与李素雅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充满了波折和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冯源、陈嘉南的爱情,都存在与女方整个家庭的角力,以欧阳才华和李宝军为代表的父亲,对子女的婚恋的态度,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乡村的婚恋观。在小说的最后,陈嘉南与李素雅走到了一起,而冯源在等待欧阳娴回来之际,又宿命般陷入了与欧阳慧的“谣言”之中,与当年“英雄救美”的出场形成了某种呼应,这样的安排有何深意?
莫华杰:很多人读《春潮》,就感觉像看电视剧。我写《春潮》,确实用了导演拍戏的视角去写,人物出场的布局和故事的走向,都有精心安排,增加文本的画面质感。结局也是再三思考的,为埋下命运的伏笔,我不想让冯源完美,希望他娶头脑有些问题的欧阳慧,而不是冰雪聪明的姐姐欧阳娴。这样更能考验人性,更能阐释主角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每个人都向往完美的生活,可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要守住内心是很难的,但我们必须要守住。
很多读者也都在问我,《春潮》第二部什么时候出来,冯源和欧阳娴最后有没有在一起。也就是说,结尾的某种呼应,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我也一直思考怎么写第二部,甚至想到了第二部的时间线索要放在现代,《春潮》男女主人公的孩子都长大了,正是回家乡创业的大好时机,实现乡村振兴。
周聪:冯源和陈嘉南的创业史是《春潮》重要的一笔,他们从捞渣工干起,贩卖过服装,开过话梅生产的作坊,最后开办打火机厂,这两个年轻人身上有一股不甘于平凡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奋斗精神,他们勤奋、踏实、肯动脑筋,心中怀揣对事业和爱情的渴望,并把这种渴望落实到具体的日常行动之中,二人的创业史也是中国90年代经济转型期的一个缩影。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一直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思考的命题,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把时间框架放在90年代,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出生于80年代的写作者而言,在呈现这段历史时有何难度?
莫华杰:《春潮》的故事背景放在上世纪90年代,对我来说更有温度,容易写出感情。1994年,我已经10岁,正是记事的时候,对那个时代保留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次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都充满温馨。而制作话梅,到淀粉厂捞渣,也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们县城曾经从顺德搬来两个打火机工厂,后来转迁到肇庆。我第一次外出打工就是去肇庆的打火机厂,干了两年。《春潮》里的故事对我而言,写起来并没有难度,甚至像命中注定一样。
周聪:在《赊佛》《春潮》《世界微尘里》之后,据说你创作了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特殊使命》,在我看来,摆脱工厂经验与“新工人文学”的固化标签,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从历史中挖掘写作的素材,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能否谈谈你接下来的写作打算,不一定具体到作品,我知道你对影视编剧也颇感兴趣,曾导演过《恶魔传说》,接下来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划,可以展开聊一聊。
莫华杰:2015年7月,我从工厂离职,成为自由撰稿人。说得难听一点,其实就是无业游民。我要养孩子,还要供房和养车,妻子是家庭主妇,并且打算生二胎。生活成本高,压力大,靠写纯文学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所以我就跟朋友开了一家影视公司,并且导演编剧过一些网络电影和纪录片。2018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读高研班,就一心一意写作,没有再搞影视。但是那两年的影视生涯,却让我知道了如何刻画人物,把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离奇。
我现在仍是靠稿费养家糊口,如果写不出赚钱的作品,生活随时都可能出现危机。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成为一名冲动的写作者,为改变现状而急功近利。我仍坚持纯文学创作,只是有意将作品影视化,希望出版的长篇小说能卖影视版权,叫好又叫座。比如《春潮》的影视版权就卖出去了,够我生二胎和两年的生活费。为了让自己的梦想仍能持续,让作品获得更多的生命力,因此在创作长篇小说时,我该下的笨功夫一点也不少,并不会因为写作遇到困难就去走偏门,或者遭遇生活危机就会在作品中迷失自己。
新的长篇小说《特殊使命》是我转型期的作品,也可能会是我的代表作。小说以东江纵队“香港大营救”历史故事为背景,加入惊险、悬疑、谍战、潜伏、动作和爱情等元素,花城出版社明年出版;而影视作品则想在香港回归30周年前完成。目前小说的影视版权已经交给上海的一家影视公司代理,希望默默耕耘中,会收获一些意外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