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文学的内面与“有我”的批评——唐诗人文学批评研讨会精要
更新时间:2020-03-26 来源:华夏杂志
王威廉:唐诗人是一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批评家,他的声音却是沉稳的,是深刻的,持续出现在文学现场,对重要的文学作品进行认真地辨析与对话,丰富的意义在他的笔下生成。他深入研究了文学的“恶”,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辨析一种当代文学写作的伦理学,具有相当的启发性,这也是中国批评家甚少关注的范畴。他对城市文学的关注也是非常及时和深入的,他关注了一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糅合的当代文学作品,发现这些作品以一种技巧上更抽象化、寓言化,思想宽度上更普遍化、综合化的故事,讲述着当代中国城市或生活在城市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性,这是很有洞见的。他还注重叙事结构的研究,他发现了许多当代小说家笔下的侦探小说叙事结构,并且构成了一种先锋性和普遍性。前者意味着侦探结构为精微的思想叙事提供了更好的故事的开展方式,后者意味着侦探的结构正在构成一种叙事的基本要素,改变了传统叙事中僵化、生硬的成分。他也是一个有着真诚品质的人文学者,他对作品尽情阐发自己的所思所想,也会努力去触碰作品的局限性,从而照亮一个更广大的思想区域。

▲唐诗人:1989年生,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陈培浩:我对唐诗人的文学批评是熟悉的,诗人虽然是个泛90后,但他的知识背景和精神立场和我们却是一脉相承,所以,我似乎一直将他视为“同时代人”,这大概是一种精神上的同时代。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唐诗人的批评著作《文学的内面》,我想先从这个题目谈起。文学的内面这个说法,首先使我们追问的便是,什么是文学的内面,什么是文学的外面?这里的内外之分,是否是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里所谓的“内/外”之分。仔细看,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之“内”指的是文本,而“外”则指向社会语境、文学制度等因素。这个划分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影响巨大,新批评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一度盛行,但这个划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从文本通往历史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新批评并非唐诗人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他之所谓文学的内面,相对的是那种非专业、不具有学理性或隔靴搔痒的“外面”,因此,诗人希望实践是一种能够把握文学内部复杂性、专业性的专深的批评。诗人的文学批评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深厚的文学理论背景,这跟诗人的求学轨迹有关,他是从硕士阶段的文艺理论专业转入博士阶段的现当代文学专业。很多没有文艺理论专业背景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缺乏理论根基,没有理论的视野和自觉,往往流于鉴赏、品评,而诗人在《文学的内面》中,显然继承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路向,对“恶”作为一个文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因此他的文学批评便在现场批评与理论纵深的两端建立了自身的张力。唐诗人文学批评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立场,这可能是受他博士导师谢有顺教授的影响,因此他并不纠缠于文学形式的细枝末节,而是关注一种文学背后的伦理难题,这便使他的批评通往了人,具有了以文学为镜像来洞察人的困境和超越的温度。我还想谈一下诗人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形象,诗人是一个相对少于言辞的人,也可以说他因为外部言语表达的减少而极大地提升了内在的表达热情,因此,他是一个内在温度非常高的批评家,这使他的写作具有了某种不顾一切的肉搏性特征,这是非常有趣的。批评家的冷凝固然有助于客观,但有时那种不顾一切的内热和肉搏也是文学批评极为重要却又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杨丹丹:唐诗人的文学批评最显著的特征是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为文学批评镶嵌上十分契合的理论框架,使文学文本的解读不再只对文本本身发声,而是对某种文学理论的文本补充和完善。但这种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的运用并没有陷入到理论的缠绕和空洞的构建中,而是能够对某种理论的起源、延伸和衍生进行仔细的辨析,从而让理论更为明晰,让阐释文本的某种理论更为贴切。
对唐诗人的这种文学批评特质的阐释,必须放置在西方文艺理论在当代境遇的背景中勘察。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随着“文化热”“哲学热”的兴起,西方文艺理论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重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在此潮流裹挟下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追逐和依附,并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自我意识的强化和对“中国性”“特殊性”“独立性”的不断阐释,中国知识界开始重估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以对抗和对立的思维去重新认知西方文艺理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质疑和解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本土性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但这种重建的前提却是放弃了从学理基础上对西方文艺理论本身进行仔细的辨识,而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先验的认为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强制阐释性,这种思维和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而唐诗人的文学批评恰恰是从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关键词的学理辨析为起点的,这种某种意义上是对新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尴尬境遇的纠偏和客观反思,只有真正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内在肌理进行辨识的基础上,才能够对其有效进行判断和甄别。例如,在唐诗人的专著《文学的内面》中,对西方文艺理论中“恶”的概念及其伦理形态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将其隐蔽的褶皱一一铺展,客观和清晰的将其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的“恶”及其伦理形态是否能在余华和苏童的文本中寻找到契合的对应物。除此以外,唐诗人的文学批评显得厚重、质朴而绵长,却略带一种偏执的气质。这与唐诗人的人生经历和身份认同存在内在的关联。

▲广东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
郑焕钊:不同于纯学院式的客观、距离的批评,诗人的批评带着自身对于世界的困惑出发,从他对张悦然的小说《茧》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祖父所遭遇的历史创伤成为一种创伤记忆,构成诗人进入文学与思想世界非常重要的内在动力,也形成他批评文字非常明显的个体介入的方式。正是这一点,潜在地决定了诗人批评的个体关切:恶及其伦理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尽管其出发点是个体的,但以恶为中心所论述的现代伦理与审美现代性问题,正是我们进入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一条极为关键的线索,它触及了先锋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写作的精神实质。诗人的评论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个体式历史体验之中,而是透过对“恶”的思想资源的清理,力图厘清恶、罪与审美的关系,并在中外现代文学的整体视野中,建构恶的审美伦理,通过对现代主义书写的“去人性化”与“非人格化”两种取向的勾连及其审美意义的讨论,他试图建立一种恶的审美伦理,以之作为评价现代写作的尺度。这正是诗人对批评理论的建构,也是理解他的批评取向的前提,他正是以此形成了对中国当代小说包括先锋小说、新潮小说等先锋策略的阐释,以及当下批评的问题取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的批评其实是有野心的 ,他正是将恶的审美伦理作为一种尺度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从中既反思了对先锋派的评价问题,也重新确立对当代文学进行评估的价值尺度。
陈崇正:唐诗人在青年评论家中格外引人注目,代表了一种新生的批评力量。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意味着有一双新的眼睛望向生产的一线。唐诗人非常勤奋,文章颇多,但多数并未结集,但我们从他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这本《文学的内面》也可以看到他研究问题的一些路径。正如书名所示,唐诗人的批评由内而外,更重视在内部进行开掘。在这本书中,他关注了“恶”这样一个大命题。对人性之恶、社会之恶推演,为他的评论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切入文本内部的角度,拨开外表纷纭的迷雾,直接探讨文本中存在的伦理、修辞和审美。唐诗人十分细密地挑开文本的肌理,试图揭开每一个脉动的秘密。生死善恶的论证对应了人物的命运,也对应了历史中浮动的尘埃。在对余华、残雪、陈希我、盛可以、王威廉、孙频、张悦然等作家的整体观察中,唐诗人透过黑暗的恶,将先锋文学中的颓废和残酷,与当下语境之下的内在欲望和外部矛盾,进行大胆地比照,从而让我们更宏观地看到一个覆盖几代作家和作品的恶之谱系。唐诗人勤奋而低调,话不多,当众说话声音也很低,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声音。他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沉稳,而这种沉稳和周到也可以在他的文字中被看见。与文学创作一样,评论写作也有许多驳杂的地图,唯有清醒的人可以辨认方向,走出自己的路来。唐诗人在他对“恶”的探讨和演练中,让我们看到他的方向感和前瞻性,也看到他作为一个青年评论家壮阔的未来。
冯娜:唐诗人的批评首先让我感到是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老成”和“执着”,甚至带着一种执拗的、“死磕到底”的钻研精神。他在新书《文学的内面》中关于“恶”的研究第一句就很打动我:“关于‘恶’的知识,我们其实是非常匮乏的。”关于“恶”,我们确实了解得很少,它不仅是日常伦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学性的以及审美层面上的,唐诗人在这个在我看来很“艰难”的命题中一意孤行,他以细微的笔触展露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人文的关怀,更从生命意识的投射中去探讨不同层面、不同形式和内涵的“恶”。不同时代和社会语境中的“恶”必然是不一样的,文学艺术本身也在更加细化地表述这些差异,我想唐诗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持续深入的,其特殊的学理价值也会不断彰显。唐诗人对一部作品背后的精神底色和生命意志是十分关注的,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内面”,是藏在海水底下的冰山。他在一篇评论小说家蔡东《我想要的一天》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现代’的袭击下,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真的能找到可以安放的‘福地’吗?这都是深藏于我们内心的巨大疑问,但小说并非要解决问题。”在现代的书写中,我们的肉体如何安放 、我们的灵魂何去何从,我想这是小说家和批评家都要面临的拷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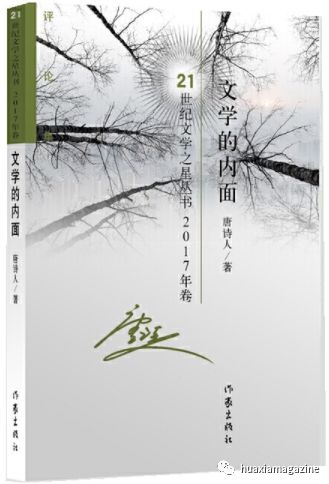
唐诗人:感谢各位对我这些文章的点评,我觉得大家的发言都特别走心,其中很多观点与其说是对我文章的嘉许,不如说是对一种文学批评写作可能性的期待吧,非常感动,谢谢!我的评论集叫《文学的内面》,这个“内”不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上的“内部研究”之“内”,而是文学之为人学意义上的“人心”之内。我们掌握了很多文学知识,但我始终相信文学从根本上而言是源于人心的表达需要。不仅文学,文学评论创作也一样,也离不开我们“内心”的表达欲。我个人投身于文学行业,尤其走入文学批评创作领域,有一个最大的心理起点,就是我读到令我感动、震惊、深思的文学作品时,内心是会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的。我想要把自己的感觉很细致很清晰地表达出来,同时也想借着这种表达同他人实现心灵的呼应和对话。而当这种表达受阻的时候,比如如何表达我的阅读感受以及我所表达出来的观点不被认同的时候,我就特别需要征用“知识”来帮助我。我的评论文章强调“个人感受”,但我又钟情于学院式批评,我是想把这两种批评综合起来。感受型批评和学院型批评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相互冲突的,但我觉得可以综合起来,我所理想的评论写作是用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相关知识来论证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那份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我们有怎样的阅读感觉,就应该遵从它、善待它,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最自然的内心的声音。当一种真实感受被压抑被否定时,评论家有责任去为它发声,这也是文学批评的个人性和公共性所在。我主张一种“有我的”“有感觉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我们学习、掌握各种文学相关知识,不只是为某种“知识”服务,是为我们最内在、最真实的文学感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