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孟繁华 | 她小说的现代气质是因为有了光 ——评蔡东的小说集《星辰书》
更新时间:2020-03-17 来源: 扬子江文学评论
蔡东的小说不是关乎信仰、彼岸、正义、终极关怀等宏大内容的小说。当然,我们需要这类小说,那些具有宏大话语操控能力的作家作品,曾经给过我们血脉偾张的激动,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但是,当唯一的讲述方式渐次消退之后,无数种讲述方式大面积复活。被宏大话语覆盖的生活细小浪花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潮流——我们身边流淌的就是这些细小浪花构成的生活潮流。于是我们发现,关于生活、关于人的情感、情绪等内宇宙是如此的浩瀚丰富。蔡东的小说更多的就是面对人的内宇宙展开的。这部命名为《星辰书》的小说集,一如它的讲述者,内敛、低调,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情感以及与人的精神领域有关的问题,读过之后竟如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因此,于蔡东和《星辰书》来说——无须高声语,亦可摘星辰。见微知著是蔡东《星辰书》的一大特点,她以丰富的直觉或魔幻、或荒诞、或洞心戳目般地讲述了她的人物的情感危机或内在焦虑,让我们感知的是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困境和难题。因此《星辰书》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报告;另一方面,蔡东又以她的方式处理或化解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幽微处。因此,她的小说是有光的小说,这个光,就是心有大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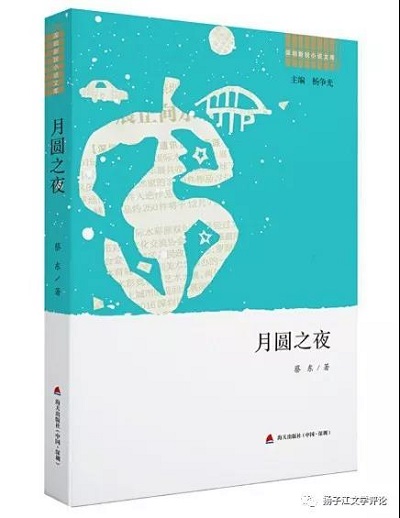
一、荒寒冷漠处更有春暖花开
几年前,我曾分析过方方发表的中篇小说《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情感故事:瑶琴姑娘死心塌地爱上了她的“白马王子”杨景国。在爱情即将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前夕,杨景国死于突如其来的车祸。与杨景国同时死于非命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子。从此,灾难如阴影挥之难去。直到中年,她又结识了一个男人,但无论这个男人如何爱她,她都难以让生活重新开始。当她最后一次去墓地告别旧情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候,得知多年前杨景国死亡的真相,让她不慎落下的擀面杖又使第二个男人死于非命——当年,就是这个男人的妻子与杨景国死于同一场车祸!而同样悲痛欲绝的男人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实在忘不掉那就不忘吧!”小说发表后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转载、评论,一时蔚为大观。方方写了一个惊涛裂岸的与情爱有关的故事,但小说写了人性的两面性:背叛与真情。杨景国是一个猥琐的男人,但瑶琴对爱情的执着像火光一样照亮了这个小说。方方的这篇小说的发表距今已过去十多年,但小说对这一情感领域的书写仍如火如荼居高不下。当然,没有什么题材比情感更适于小说。但我们发现,十年之后,对情爱的书写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薄情、背叛、算计、欺骗、冷漠而没有爱情。小说写的都与情和爱有关,但都是同床异梦、危机四伏。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生活总有不如意甚至不堪忍受的苦楚或难处,蔡东同样也在面对。但蔡东讲述这些背面生活时,却没有写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那些不忍处她节制且体恤。那是了然于心后的体悟,是对生活光景的善意修复,就像德高的医生发现了病变,并不是一惊一乍而是得体或无声地疗治。蔡东对生活的理解,就像加缪一样: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将结束。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的渴望将宣告一切已结束,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伶仃》中被抛弃的妻子卫巧蓉,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丈夫出走后,她不惜跟踪丈夫,但丈夫确实洁身自好,事情不是她想象的样子。小说以极端的方式写了丈夫出走后卫巧蓉的“伶仃”况味。当一切大白,卫巧蓉与生活和解了:“他们至今没有碰过面。她设想过面对面遇上的情景,这辈子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她不知道该对他说点什么,但她还会迎上去,向他问声好。”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山峦连绵,白云飘过,青山依旧在,万事万物都没有改变。但对卫巧蓉来说“身边的黑暗变轻了”。经历过了,从容不迫才会成为人生一场真正的幽默,她无须安眠药也可以轻松入眠。放弃怨恨和猜忌,与生活和解,就是作家赋予《伶仃》的一缕阳光。中篇小说《来访者》是《星辰书》中权重较大的一篇作品。小说讲述者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或治疗者,她的对象名曰江恺。对这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庄玉茹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在帮助江恺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江恺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因此这是一篇平行视角讲述的小说。江恺患病的根源以及疗治过程非常缓慢,一如石子投入湖中,层层波纹渐次荡漾。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庄玉茹,虽然专业但也未免紧张,但她就是江恺的阳光,她终要照耀到江恺内心的黑暗处。她不是抽象的理解和同情,这与具体疗治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她如何通过具体的细节和办法让这个貌似“活得不错的人”走出黑暗。当然这是心理咨询师庄玉茹的工作。对于作家来说,在注意技术层面循规蹈矩的同时,她更要关心怎样塑造人物,怎样让事件具有文学性。这时我们看到,庄玉茹居然陪着江恺去了一趟洛阳——江恺的老家。这个事件是小说最重要的情节。时间回溯了,江恺重新经历了过去,然后那些美好与不快逐一重临。那扇关闭心灵的大门终于重启。但我更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他们来到白马寺,寺门已关,游荡中他们发现了一家小酒馆,于是他们走了进去——
我们商量着点菜,芹菜炝花生、小酥肉、焦炸丸子、蒸槐花,主食要了半打锅贴。菜单翻过来有糯米酒,我问他:“喝点酒吗?”他笑笑:“度数不高可以。”
很快,店家温了一壶酒上来,酒壶旁是一个小瓷碟,放着干桂花。我先把酒倒在杯子里,再撒上厚厚一层桂花。乳白色叠着金黄色,米酒的酒香托着桂花的甜香,在不大的屋子里漫溢着。
这是一个寻常的生活场景,我们曾无数次地亲历,因此一点也不陌生。但这个场景弥漫的温暖、温馨和讲述出的那种精致,却让我们怦然心动——谁还会对这生活不再热爱。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疗治,也就是庄玉茹走出小酒馆才意识到的“一次艺术疗治”。庄玉茹是江恺走出黑暗的阳光,这缕阳光与其说是专业,毋宁说是她对生活的爱意置换了江恺过去的创伤记忆。在一次访谈中蔡东说:“对日常持久的热情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发现,才是小说家真正的家底。人生的意义何在,毛姆用《刀锋》这样一部很啰唆的长篇来追问,小说里几个人物分别代表了几种活法,伊格尔顿用学术的方式来探讨,答案不重要,他的逻辑和推进方式让人着迷。而我写下的人物用他们的经历作出回答:意义不在重大的事项里,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庸常中。就像我在《来访者》里写下的一句话:在最高的层面上接受万物本空,具体的生活中却眷恋人间烟火并深知这是最珍贵的养分。”这不止是她的宣言,更是她在小说中践行的生活信念。因此,当江恺的妻子于小雪说庄玉茹救了一个患者时,庄玉茹摇头说:“救了她的是流逝的时间,是男欢女爱一日三餐,是贪生和恋世的好品质。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最有魔力的。”作家的健康赋予了人物的健康。谁都会面临无常,但对健康的人来说,一切过去便轮回不在。于是,小说结束时庄玉茹的“这世界真好,生而为人真好”,就不是一种空泛抽象的感慨,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恩,犹如爱的七色彩练横空高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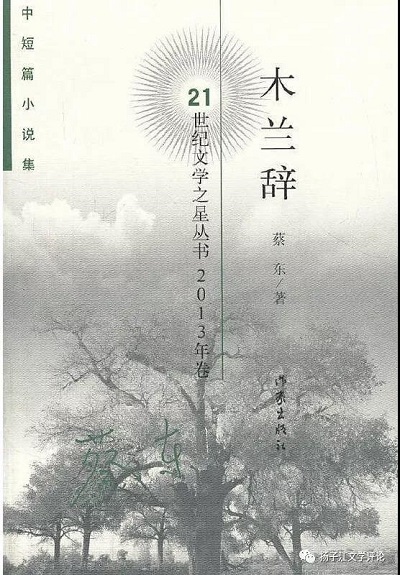
二、“现代气质”与小说的难度
蔡东的小说有鲜明的现代气质。这个现代气质不只是说她小说具有的时代性或辨识度,我指的是她小说人物的性格。《天元》,应该是一部寓言小说,一部具有鲜明“现代派”气质的小说。陈飞白是个人才,但她入职每次都折戟在面试上,她不得不从事一般性的工作而难以介入中心。所谓“天元”,就是围棋盘正中央的星位,也是众星托衬的“北极星”,是最耀眼的一颗星,天元也意指那些超神入化的人物。而陈飞白应该是一个“此辈不可理喻;亦不足深诘也”的人物。她不想成为“天元”,不想成为那个世俗意义上于贝贝式的成功人物。她更像是来自彼得堡时代的“多余的人”,现代中国的“零余者”或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反抗者。不同的是,陈飞白并不狰狞铁血,她表面略有棱角内心坚不可摧。在她的观念里:
我终于不是少年也不是青年了,
不再因年龄被强行划入一场场比赛
回望这些年,我会从心底笑出来
我记得
我活得特别有兴致在每一次能瞄准的时候我没有瞄准
我往左边或右边偏了一下
因为这不瞄准
因为这不瞄准
我觉得,我是一颗星我是一个人才
我活着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次的不瞄准
这就是陈飞白的诗。她值得炫耀或自我确认的就是一次次的不瞄准,她就是要特立独行。甚至她的这一节诗歌,也只用了一个标点。当然,决绝的是陈飞白而不是蔡东。蔡东开篇不久即写到一条抹香鲸的死亡。离开了大海,离开了具体的生存环境,即便你是一个庞然大物,也难逃厄运。
《照夜白》中的谢梦锦,是一个一心要“逃离”的人。“逃离”是加拿大诺奖获奖作家爱丽丝·门罗的小说。距门罗更为久远的时代,女性就早已准备好了“逃离”。因此“逃离”是女性文学屡试不爽的主题。面对旷日持久言不由衷的课堂,谢梦锦几乎忍无可忍。于是她“失声”了,她可以不上课了。“喜从天降”的“失声”让谢梦锦自由了。自由太让人神往了——歌德说:“为生活和自由而奋斗的人,才享有生活和自由”,斯宾诺莎说:“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谢梦锦不想奋斗也不想当巨人和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于是,做一个人的幻想便出现了:
我一直有个愿望,或者说幻想。有一天我到了教室,坐下来,不说话学生也不说话,大家就这样一起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铃响了,所有的人一言不发,寂然散去。
但是,谢梦锦并不是一个彻底反抗的“现代主义者”。她马上说:“想想罢了,怎么可能,一大群人呢。说不说话,从来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与其说谢梦锦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毋宁说蔡东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那个时代毕竟只可想象难再重临。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适可而止”。陈飞白、谢梦锦都生活在既定的生活环境中,她们具有的“现代气质”已实属不易。利奥塔在《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中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文化是身处根本处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们是出生,死亡,爱情,工作,生孩子,被实体化,衰老,言谈。人们必须出生死亡,等等。于是一个民族对这些人物,这些召唤,以及它对它们的理解,做出了回应。这种理解,这种倾听,还有赋予它的回声,是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它对它自身的理解,它的凝聚力。文化不是归属于根本处境的习俗,计划或契约为基础的意义系统;它是民族的存在。”因此,讨论陈飞白、谢梦锦的“现代气质”,离开了利奥塔的民族的文化处境或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说不清楚的。蔡东的“现代气质”就蕴含在这一文化处境和场域中。
有难度的小说,就是用爱化解人的无尽苦难和痛楚。痛苦是人类永恒面对的景况,用想象的方式解除人的痛苦并走出这一境遇,是有爱的作家选择的春冰虎尾的道路,也是一条难以为继的道路。它极易形成模式或同质化,即便确乎不拔也险象环生。但小说就是冒险的艺术,绝处逢生也就成就了一个作家的伟力。我们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包括那些内心深层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通过与别人别处的生活比较呈现的。因此,那些理论金句尽管必要,却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作家对具体生活场景和人物内心细微的描摹,一切竟一目了然一览无余。我们知道了自己那些幽微隐秘的痛楚究竟在何处作祟,找不到的那些痛点就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切肤之痛就这样如期而至。读蔡东小说的致命感受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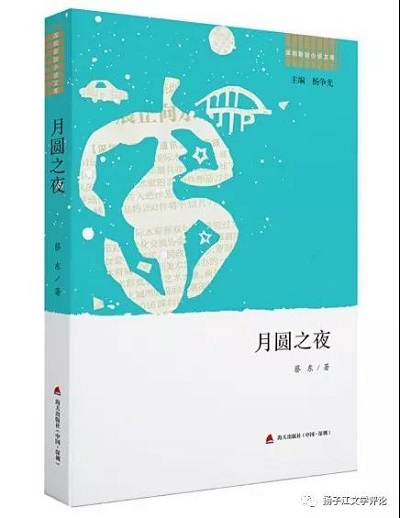
之所以说发现、捕捉的是人的情感或感觉的幽微处是小说的难度,因为那是一闪即逝却又挥之难去的感觉,似有若无又无处不在,它几乎成了一个人的魔咒或幽灵,游荡在人的内心深处又不时泛起。那种只为别人观看的“盆景”式生活在传染般地蔓延。《出入》中的梅杨一直生活在朋友李卫红的阴影下,鄙视她愤恨她,却又受虐癖般地不能停止接近她。林君梅杨夫妇话不投机,旅游计划搁浅,不谋而合的竟是源于两个人均难以启齿地对分开的渴望。也许这时我们才会理解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背后的一言难尽。夫妇均有对“分开的渴望”,就是人物内心的幽微处。这是生活中几乎人人都有又难以启齿的心理活动,如果诉诸实践,也不啻为医治夫妻矛盾的一剂良药。这里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但这里的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不然就不能解释《出入》中的林君的“临时出家”,以及“出家班成员”们相互间亦有“咫尺天涯”的美妙感了。那个混乱的所在,基督教、道教、佛教一应俱全,国人女翻译、洋人牧师悉数在场。这个反讽的荒诞场景将精神世界的无序混乱和盘托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梅杨居然对林君说“我可是修成正果了”。出与入,居与处,是传统士阶层难以处理和选择的矛盾,但历史发展至今日,这个曾经犹疑不决的矛盾终于幻化为一个后现代的闹剧。
《布衣之诗》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孟九渊和妻子赵婵分居前曾宴请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席间大家言谈举止得体周正。但结账时——
赵婵提出打包。孟九渊用眼神质疑她,你这是怎么了?拿回家你吃吗?吃吗?赵婵避开他的目光,起身去柜台付钱,很快就有服务员来桌旁收湿纸巾。孟九渊按住湿纸巾,问:干嘛?服务员缩回手去,解释道:“女士说了,没用的都退掉。”同学们赶紧拿起来,说:“不习惯用这个,退了吧。”孟九渊动作很大地扯开包装,说:“我用”。
但回家的路上俩人并没有争吵,默默不语沮丧茫然。这最后一刻让宴请毫无颜面。这个细微处,赵婵的性格和两人的关系,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生活自有迷人的魅力。但生活中总要遭遇它的背面,就是那些琐屑、无聊甚至构成“敌对性”的阵势。它让生活变成煎熬、无望甚至绝望。生活中某些细小的缠绕、纠结、不快等,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和情感,处理的过程并不亚于面对“大事件”时的犹豫或举棋不定。在大的生活内容面前,我们有那些高明的向导或潜在向导,他们代替了我们思考;我们还可以选择从众——或者有人先于我们选择,他们可以提供某种参照。但面对个人生活的百态千姿,你必须自己拿主意。这时你拥有了自由,也因为自由你拥有了麻烦——无所适从的麻烦。这个麻烦与生活丧失了方向感有关系,但是,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方向感有关,其间的不确定性如影随形挥之难去。蔡东的小说要处理的大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这就是蔡东小说的当下性。
《天元》中的陈飞白虽然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但她非常在乎和丈夫何知微的情感。她是太爱何知微了。两人的关系即便如此,仍有需要小心翼翼的缝隙。陈飞白曾经问何知微“喜欢你现在的工作?足以安身立命?”他们的价值观显然并不严丝合缝。何知微也爱惜和陈飞白有关的一切,他突然有些担心,“万一,他和她,把话都说完了怎么办?会有没话说的那一天吗?不敢深想,只能珍视此刻,想着既有此刻,也不算白活了”。彼此情感甚笃相爱甚深的人,也未必相知彼此。所谓“心心相印”不过是句堂皇的修辞而已。蔡东对人心内部秘密或细微处的大胆敞开或剖析,是她小说最具力量的一部分。温文尔雅是小说的表面,犀利就在其间。

三、对“不中用的东西”的发现
但是,《星辰书》终是一部心有大爱的书。这个爱,不只是对人物的处理,亦隐含在诸多细节之中。除了人物关系之外,那些鸟语花香的细节更是楚楚动人。《照夜白》中的谢梦锦,“按照今天的设置,她不能发出声音,这番话只是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她想起家里的柜子抽屉里,放满了杯壶碗碟,几年也用不上一回的,就是为了看看,看着喜欢。她从小喜欢的,好像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一路上她车开得很快,急切地想把刚才的夜晚甩到身后。再转一个弯就到小区了,每次先看到的都是裙楼的鲜花店,她把车速降下来。店里的灯还亮着,她停下车,看着店员把摆放在门口的花盆一一搬进店内,透过落地玻璃,能看到不大的空间里布满鲜花。当初花店刚开的时候,她担心花店生意清淡,万一哪天关门就可惜了,她是第一批办储值卡的人。毕竟,楼下开间花店,住户的日常里就有了点高于生活的东西。”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高于生活的东西”。谢梦锦因对生活的这些感知和认识,人物就有了站位,她的“失声”和对日复一日机械生活的反抗,就有了意味——她抗拒的是被生活的“异化”,却坚决站在了“美”的一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在“不中用的东西”中腾空而起,一如画中的骏马“照夜白”。蔡东小说中那“不中用的东西”“高于生活的东西”比比皆是。无论是人物趣味还是讲述者趣味大抵如是。《伶仃》的开篇——
黄昏的时候,卫巧蓉走进一片水杉林。通往树林深处的小路逐渐变细,青苔从树下蔓延到路边,她快步走过时,脚步带起了风,缕缕青色的烟从地面上升起,蜿蜒而上,越来越淡,越来越清瘦。她停下来,等烟散尽了才俯低身子凑近看。这些日子阳光好,苔藓干透了,粉末般松散地铺展着,细看起来如一层毛毛碎碎的绿雪,她小心喘着气,担心用力呼出一口气就会把它们吹扬起来。
然后卫巧蓉走出了树林,天空、小径、街道、楼房、海岸线、山丘和翻过山头的一朵云,伸向天空几个角的剧院才渐次出现。这些貌似闲笔的文字,让小说松弛冲淡。但小说内在的紧张就蕴含在从容的文字中。被“窥视”的丈夫一无所知,窥视者卫巧蓉则一览无余。那些“不中用”的闲笔便具有了“张力”的意义。《天元》中何知微一直期待将地铁六号线上印有“一步制胜”的广告牌摘走。女友陈飞白曾经做过这件事并且成功地把广告牌取走了。轮到何知微却遇到了麻烦。事情不在于何知微是否能够摘走广告牌,即便摘走“一步到位”的广告牌,陈飞白的命运能够改变吗?但是有了这个情节,小说便飞翔了起来,小说有了诗意。那是一种对“天元”的反抗,对“现代”价值观和格式化生活“理想”的反抗。
“不中用的东西”,一如加缪旅途中将风景化为内心的背景,一道微光,一首乐曲或一群拔地而起的飞鸽,让他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欢乐。如是,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梭罗会守着一潭湖水,梵高会画一双农鞋或几枝向日葵,诗人要吟唱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对“不中用东西”的迷恋,只因为那是“高于生活”的美,是精神需求的要义。无论人的自然属性是否被满足,是那些“不中用的东西”改变了我们。有人曾打比方说,家里最有用的东西是厨房和厕所,但是有客人来了,你让客人看的或者是一幅画,或者是进书房,这画和书是没用的。但你不会领着客人去看你的厨房和厕所。
我还注意到,蔡东的小说对日常性生活的兴致盎然。她的小说,几乎每篇都会写到花花草草,写到与日常生活的必须,写各种菜蔬或餐桌:
吃过早饭,她瞒着给女儿检查行李,钥匙,证件。女儿呢,忙着检阅冰箱,里面满满当当的是蔬菜、鱼虾和水果,冷冻层里也塞满水饺、猪肉包和带鱼段。
早市海鲜区堆满了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梭子蟹、海虹、毛蛤、爬虾,地面上水淋淋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鲜的味道。
——《伶仃》
两人一路引我来到小区,小区的建筑物很疏朗,花园开阔,种着些合欢、夹竹桃、石榴、垂丝海棠,地上除了草坪还有大片的毛牡丹和矮牵牛,水系景观也愉人眼目,防腐木的平台,曲水游廊连起几座小巧的六角凉亭,岸边随意散落着几块景观石,流水潺潺,红红白白的锦鲤在硬币大小的绿萍间游弋。
我早早来到咨询室,把洛阳买的牡丹绢花插在藤筐里。花朵绣球般大,颜色是渐变的粉,只有一瓣显得各色,近于深红,像湿了的胭脂,红色冷不丁一大步跳到粉白,倒是一点也不呆。
——《来访者》

这些笔墨,既是闲笔,是“不中用的东西”,是生活的情怀也是个人趣味,一个女性作家的性别区隔亦在这情怀和趣味之中,或曰对生命的体验之中。小说考量的最终还是作家对生命理解的深度。蔡东自己曾说:“说到‘我想要的一天’,在非常不确定的世界里,有闲暇的一天大概便是最好的一天了。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可以收拾收拾屋子,可以去菜市场逛上两个小时,买好菜回家做顿饭,可以拿起一本读过很多遍的书,从随便翻到的那一页开始看,毫无功利性地散漫地看。这就足够了。”正是有了这等平常心,蔡东才有了她和小说的低调内敛。但蔡东的内敛或低调,不是张爱玲见到胡兰成的那种“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卑微甚至不惜失了主体性。蔡东是《照夜白》中的谢梦锦喜欢的铃兰花,在盛年时便向下绽放,不似那些仰着头向上开的花,残败了才无奈地低下头。铃兰是主动、自愿地低头俯看,把花开向地面。开向地面的绽放也可以大放异彩,只不过那需不同的看客或听众罢了,一如“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的高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