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申霞艳 |勘探都市人的内心——张欣小说论
更新时间:2020-03-11 作者:申霞艳 来源:文学报
城市文化的包容给了女性更开阔的生长空间,让大家更好地自我实现。在广州都市文化的建构中,张欣弦歌不息,持续地捕捉这座城市的变化,她的写作策略的调整也与这座城市务实的气质密切相关。
张欣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改革开放后走上写作道路,努力切近这座城市的灵魂。张欣具有很强的生活智慧,很多事情都可以咨询她。她谈吐大方,穿着知性,骨子里有着军人的利索,抑制不住的干劲让她充满活力。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肇始之地。一方面华侨的足迹遍天下,广交会与诸多国家有频密的商业交往,另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内地的打工者、创业者。

张欣说:“广州是一个故事特别多的地方。作为职业小说家,很多事情我会以写作者的眼光去看,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灵感实际就在生活中,只要你能够去感受,背包去采风是下生活,但是跟朋友一起流眼泪也是下生活,你能感受到故事,就会变成作品。”张欣爱着生机勃勃的广州,这种爱融入她的书写,影响了许多年轻人。

刻画都市女性的艰难成长
经过初期的艰苦摸索,张欣将目光锁定在都市职业女性的刻画上,那些在商海沉浮中努力打拼的女性从那些苦苦执着于情海的女性中脱颖而出,她们有了新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现代女性一扫子君、祥林嫂等散发的麻木无奈气息,她们卓然而立,有自己的主心骨,如《千万与春住》中的夏语冰、滕纳蜜,《首席》中的飘雪和梦烟,《如戏》中的叶佳希,《不在梅边在柳边》中的蒲刃、梅金、柳乔乔,《锁春记》中的庄芷言,《狐步杀》中的苏而已等等。女性能够活得精彩纷呈,这既是现代启蒙的力量,也是都市的力量,是广州给予女性的礼物。张欣在小说中歌颂:自尊、自强、不依傍,不屈服,尽管受到命运的百般嘲弄,依然像荷花一样不蔓不枝,像梅花一样经冬傲雪,她们为自我实现所经受的精神之苦并不比那些饥饿之于肉身之苦逊色。大城市、高科技的发展正在为女性的独立提供越来越重要的依凭,比如我们习惯的快递就极大地缓解了搬运重物带来的不便。但是光有科技是不够的,光有金钱同样是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开放让我们拥有新的精神来打破陈旧的精神枷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剧《外来妹》、流行歌曲《心雨》、《你在他乡还好吗》等等风靡一时,让广州在都市文化方面引人注目,地利人和,造就了一批歌星、影星、名主持、名记者以及经纪人、广告达人。各行各业的弄潮儿应运而生,造星、追星也盛极一时,明星以与大众的亲密接触、对话互动挑战精英文化。
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小说的典型作用就在于记录势利行为所生发出的幻想,并试图洞察隐藏在所有虚伪表象之下的事实。”
人性中的势利,小说家要迎上去探个究竟。人的自我认同一部分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哲学家康德也谈到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社会化和自我化。势利会从人类的群体性本能中流露,张欣如何在写作中因势利导和剖析?
张欣写得最多的是大众文化催生的新的群体:歌星、影星、模特儿,老一代艺术家如何对待新的商业文化,揭示了时代变化导致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蜕变:《窑艺》中讲述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天之骄子曹天际和叶一帆南下广州,在广告业打拼出自己的天空;《掘金时代》刻画了编辑部主任姚宗民如何抓住转型时机,出版社创造新的盈利模式;《浮华背后》中影星莫亿亿靠委身于人而一夜走红,最终走上了不归途,《伴你到黎明》《沉星档案》也写到演艺界的光怪陆离。城市既给了他们物质的欢悦,也给了他们精神的流离。
张欣的《岁月无敌》以广州的流行音乐界为背景,讲述方佩和千姿母女两代在事业和爱情两方面的异同与传承,旁及形形色色奋斗在演艺界的歌星和音乐制作人。纯粹的艺术家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人生和艺术原则的固执与坚守,她们清洁的人格力量;而在千姿身上,我们既看到时代风雨让她迷茫,也看到老艺术家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使她终于不致迷失,不至于胡乱挥霍青春,最终凭人格魅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歌唱家方佩在给女儿千姿的遗信中写道:
你要学会爱的能力,但不要相信爱的神话。爱是一种牺牲,爱是一种包容。金钱是重要的,但是它并不值得我们拿出整个生命和全部情感去下注,如果你轻易取舍,它会轻易夺取你一生的幸福。
方佩这封信涉及到爱、金钱、人生的大原则,也可以视为张欣的人生信条,这支持她认同的人物在瞬息万变的都市,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活出真我。程文超认为张欣的创作是欲海里的“诗情守望”,雷达评价张欣为“一脉生机勃勃的独流”,“她的语言建构了一种契合都市语境的特有的抒情风格,一种古典美与现代流行话语相糅合的情调,打造出一种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时尚化写作模式。于是,在当时新都市小说初兴的大大小小作者中,张欣是个独特的存在,为市民读者所喜爱。”贺绍俊在《铸造优雅、高贵和诗意的审美趣味》中谈道:“我非常看重张欣对于当代都市小说的建设性努力。”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在当代文学中探索着前行,张欣是有影响力的探索者,她的小说没有沉湎于都市纸醉金迷的物欲诱惑之中,她对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被遗弃的精神性特别在意,她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荡漾,这种贵族气质也许在张欣最初的写作中只是一种文化趣味上的无意流露,还是一种感性化的东西。而随着写作的积淀,这种文化趣味逐渐凝聚成一种审美精神,一种人格范式。“诗情”、“独流”、“贵族气质”,评论家都注意到张欣创作的独特性,肯定她为都市文学建构所做出的努力。
如果用关键词来浓缩,张欣使用的是几味常用药:商海沉浮、职业女性、爱恨情愁……并无特殊的偏方,但张欣是时代的暖心人,她呈现了主角在不同的行业打拼挣扎,比如《首席》写的是玩具制造业,《绝非偶然》写的是广告业,《如戏》写的是服装设计师,《浮华背后》写到走私与缉私,《沉星档案》写新闻主持人,《深喉》写报业传媒……《狐步杀》、《黎曼猜想》和《千万与春住》等长篇诸多人物在不同的行业交集。从这个罗列的简要清单能发现张欣是一位心灵敞开的观察者,她深入城市内部,赞美这开放时代,赞美每一个不曾辜负的春天和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为这些背井离乡的创业者留下心灵剪影,她说:
我的心愿是走进都市人的内心……都市人内心的焦虑、疲惫、孤独和无奈,有的真是难以排遣的,所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他们开一扇小小的天窗,透透气。
张欣积极地生活、观察、体验,积攒多方面的知识并体验各种职业者的情感,这是她写作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张欣以写作肯定了普通劳作者的价值,并扩大了劳作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她刻画了女性艰难的成长,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轨迹,如果没有文学作品为其背书,就会淹没在时光的河流中。

走出经验藩篱和纯文学幻觉
从张欣小说人物精神成长的意义可见她写作的时代性和都市性。漫长的农业文明决定了乡土文学的非凡意义,而乡土文学遵循的宗族伦理,是熟人社会世代更迭的规则。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的生存格局,“乡土中国”逐渐被城市中国替代。都市开启了陌生人社会,都市聚合的原则是合作而非血缘,这就让大家都有了交往的界限和各自的生活空间,现代都市客观上促进了个体的自立与成长。
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更多人居住的处所,当馒头问题解决之后,人类的精神难题就更为突兀地呈现出来,苦闷、迷茫、孤独、焦虑等等情绪正是现代主义书写的核心。张欣很快就捕捉到这一点,在《记录生活而已》中她写道:
都市生活的真正的内核是探寻不尽的,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浮华的热闹,常常是火树银花掩去了许多心酸与悲苦。
她致力于从繁花般的都市景致中探求人的“心酸与悲苦”。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私人化叙事、“小女人散文”盛行时,她并没有搭这顺风车,她独立探求的是女性精神的更新与开放时代、前沿都市的关系,她所勘探的是人的自立与自我的成长。张欣渴望拓宽女性的精神世界,让女性有勇气在更为辽阔的疆域闯荡。
张欣郑重地写下《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小说从根本上斩断了女性对于爱情的幻觉,质疑建基于农业文明伦理基础上的爱情定律。如果将爱情和事业比喻为人的两条腿,那么,张欣笔下的人物往往以事业为右腿。当我们稍息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将身体的重心挪移到右腿上,日久月深,右腿的支撑力大大地强于左腿。
在这个朝夕变化的世界上,爱非常困难,爱情像花香一样袭人,前提是在吃饱喝足后才闻得到。有的文学作品在强化男权思想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流行爱情小说曾经风靡一时,其中包含的“致幻剂”让少女们沉迷于不切实际的白马王子想象中,而忽略生活本真的内核,爱情幻想无法承载起生命的重量。生活世界的一切难题都得靠自己去攻克,女性一点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斩断对易变的情感关系的精神依附。
“川流不息的”三餐就足以让人抛弃幻想。受岭南“揾实”文化的影响,即使是非常传奇的故事和抒情的风格,张欣也为之注入写实的灵魂,自立、自尊始终是她所认同的品格。九十年代后期,她对写作做出调整,更关注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从新闻事件中汲取素材,大量写作长篇,人物、故事和意蕴更为复杂,以草蛇灰线的方式碰触都市的丛林法则;同时将严肃文学的使命意识与大众阅读要求的轻松莞尔融合,积极关注消费社会的变化,探求读者关心的写作资源。她说“我已厌倦那种圈里写,圈内读,而后相互欣赏的文学。文学在我心中,必定要有一定的民众性……所以我只要求自己写的小说好读、好看,道出真情。”张欣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写作不是象牙塔中的自娱自乐,首先要好读、可看。《浮华背后》《沉星档案》和《深喉》等作品脱胎于真实的新闻事件,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颇受观众喜爱。
其实以小说贴近新闻不过是题材的来源而已,值得谈论的是她的叙事用心和态度,这些作品标志着她从自己熟悉的文艺界走向更为阔大的社会生活。女作家最受诟病的是经验写作,不断走出写作舒适区、观察众生和万物是张欣能够成功突围并持续创作的原因。最引发想象力的永远是真实的生活,五彩缤纷的现实催生了五花八门的小说。只要你勇敢地置身于生活的激流中,想象力就不会衰颓。
开放时代敞亮了“诗和远方”,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不少出色的女政治家、科学家、创业者;文化、传媒、教育、商业甚至IT等各行各业都涌现了不少耀目的女性。这些女性并非千人一面,远不是“女强人”三字可以囊括。她们同样有内部的丰富性、女性的柔情和内心的哀伤。现代社会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爱情、男人、家庭并不是女性生命唯一的支点。完美的事业与幸福的爱情和家庭并不矛盾,二者都意味着对未知领域的探求,意味着向新生活挺进,追求事业的勇气和经验同样有助于追求爱情。
张欣头顶有“月亮”,但笔下并不忽视“六便士”的威力,贫穷堪称小资最大的敌人。《爱又如何》中,爱宛为了维持自己经营的商场,答应当自己初恋的情人以求不被抛弃。《岁月无敌》中的歌星为走红而委身于香港老板……金钱的威力无处不在,金钱在无形中撬动着人物的思维。都市最光鲜的部分:琳琅满目的高级商场、富丽堂皇的星级酒店、昂贵精美的奢侈品、香甜可口的小点心和缩在街角的小饭馆……都在她的小说中占据一席之地。要给人物毫发毕现的生活环境,就像土地才能让种子生长,衣食住行让人生落实,就像广州世袭的喝早茶、煲靓汤一样,我们以一缕缕茶雾抵御外部时光的直入。对饮食起居等细节的描绘也慢慢形塑了都市文学的样貌,人物的诸种感情也与之匹配。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乡土叙事中,我们可以将人物的感情附着于植物上,这种融情入景的方式已经进入民族的审美结构中,而在都市小说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必须寻求新的寄寓方法,人造之物和人文空间以及日常饮食成为人物情感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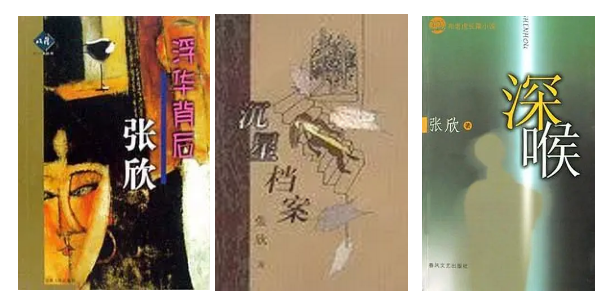
她们独自疗伤和各自成长
张欣塑造人物最为擅长的是对照法,不是黑白分明的对比,而是桃红柳绿的映衬。2019年的新作《千万与春住》延伸了两位都市职业女性并驾齐驱、终于分道扬镳的经典结构,核心是惊心动魄的现代“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辅之以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美爱情,两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共同爱上白马王子……更沉重的是与诗意渐行渐远的日常生活,是人性和神性的博弈,还有现实与历史的互动。
女主角滕纳蜜是生活中的大多数,没有闪闪发光的硬件,小小年纪就饱受了因父亲贪污下监狱的歧视,尚未成年就被父亲托付照顾好母亲的重任,深深暗恋着的男生与她频频接触,却是为了与闺蜜夏语冰暗度陈仓。仅仅为了生活,她一直在努力,纵使被学校当权者竭力排挤,也在改革中抓住时代契机,转行从事教育培训后做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贪污的恶名、残缺的父爱所致的伤口始终如影随形,纳蜜终生背负伤口前行。
闺蜜夏语冰的名字显然来自“夏虫不可语冰也”,她是集人间褒义词于一身的女神:出生于高干家庭,纯美的爱情神话的女主角,退回人间依然能够得到王子的青睐,轻而易举地被带到美国,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如此巨大的反差横亘在一对闺蜜之间,命运的敌人却不知道躲在何方。尝尽了原生家庭之苦,滕纳蜜不由得恶向胆边生,以换子来改写自己儿子的命运,让他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先是交换后的薛狮狮被人贩子偷走了,滕纳蜜的生活裂开了巨大的创口;而被交换去了美国的小桑君患上轻度自闭症,在夏语冰的精心抚养下,成了非常有教养的日本料理师傅;但丈夫怀疑夏语冰与初恋藕断丝连,偷偷做了亲子鉴定,知道小桑君不是自己的骨血之后,立即有了外遇,在维持现有婚姻的同时另生了孩子。

《千万与春住》中的滕纳蜜,这个被张欣称为“有疤的树”一样的人物,人性的复杂、人物站立在小说的最前端。这也是代表了她写作上的转变的一个人物,“结束了对纯粹人物的塑造”。
“薛狮狮”意外地找到了,这个被隐藏十多年的换子秘密也揭开了。小桑君命途尚好,有着精湛的厨艺和让人叹服的修养。而“薛狮狮”却成了乡下的王大壮,携带着童年被弃的巨大创伤。他重情义,在夏语冰的帮助下帮养母到北京,治好了病。他的命运被换子、贩卖、城乡差距永远地修改了,一切都回不去了。
夏语冰最后一无所有:昔日的家庭、爱情、丈夫、儿子,无不离她而去,但巨大的创痛也没有使她丧失理性和优雅。小说书写了人物在历经沧桑和人生挫折后,依然直立于天地间。
自幼患自闭症的小桑君因夏语冰的悉心养育,他具有清洁的心灵。小人物与大时代的隐秘勾连随之浮现,如果能够由此触及到根本性的社会结构会将小说带到新的境界,由此也能理解张欣所追求的体面二字包含着多少人的梦想。现代文明以独立为号角,唤醒每颗沉睡的心灵。都市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暗伤和隐疾,眼泪无济于事,伤口绝不能像戒指一样拿出来炫耀。都市人,如何在时间的怀抱中,自行疗愈伤口?就像阿多尼斯的诗所写:“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保持写作意味着艰难的思想训练,还有对自我重复和熟稔劳作的突围。创作数量大的作家如何能够避免重复?每个风格独具的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套路,这些招数和细节已经沉淀在潜意识中,在写作之夜自动出击,这是写作的命定。过于爱惜羽毛的作家因无法完全创新只能中途放弃。坚持终生写作,首先要战胜自身的惰性,还要发现向上的阶梯。张欣能在娴熟的写作技巧与崭新多变的都市生活中巧妙地寻求平衡,她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节奏和主题,也在从未懈怠的写作中找到了自我更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