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陈崇正︱书无非是读书人的“玩具”
更新时间:2019-06-24 作者:陈崇正 朱蓉婷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崇正家在十二楼,从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白云山。走在陈崇正家里,不见书房,也分不清哪里是书房,因为哪里都有书柜,书房与客厅功能融为一体,四五个书架,整洁干净,书籍排列比较随意。陈崇正说,相比设计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书房在客厅里的利用率更高。
作为一间文学编辑的书房,文学书自然是主角,其中有一排书架几乎全是王小波。陈崇正对记者说,自己多年来养成的癖好就是收集王小波不同版本的书,顺着这排书架往上看,另一排摆满了金庸作品集。
金庸和王小波,是陈崇正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两位启蒙者。前者是许多读书人的集体回忆,后者被誉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兄长,但对当时生活在潮州的一个小镇少年来说,并不容易读到。
2002年,正在读高三的陈崇正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王小波的名字。抱着对“王小波”的无限好奇,少年陈崇正踩着单车,走遍了潮州当时的所有书店,最后终于在一间小书店里找到了一本《青铜时代》。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这刚好是花城出版社的版本,12年后,陈崇正也到了花城出版社上班。
陈崇正还记得,那个暑假天气炎热,刚刚高考完的他,在医院陪伴一位生病住院的亲戚。病房外昏暗的走廊里,他躺在一张折叠椅上,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下读起了《青铜时代》。一本书启蒙一位少年,就像一扇门突然被打开了。
对陈崇正来说,王小波对他的影响无异于一次思维的解放,“我从金庸那里继承了一种编造故事的想象力,但是在王小波那里,他告诉我,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思维操练。这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的确,从日后《半步村叙事》到《黑镜分身术》《折叠术》这些小说里,也能看出些许痕迹,陈崇正是一个不满足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他希望将机智、困惑、审视、寓言通通“折叠”进故事的缝隙之中。
怀揣着文学梦想,陈崇正参加了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拿到了二等奖,大学毕业后,陈崇正来到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也一直持续写作。但今天回过头看,陈崇正有些“悔其少作”地说,当年写的都是青春小说,也不知道什么纯文学圈。随着年月增长,这种写作的局限逐渐显现,似乎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他眼前还有更高的山峰要去攀爬。
在中学校园里,陈崇正日常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撕裂感:白天讲解课文,那些浅显的解读和自己下班后思考的文学问题并不同步。终于在2014年,陈崇正的中篇小说《黑镜分身术》在《花城》杂志发表,随后机缘巧合,他成为《花城》杂志的编辑,离开站了八年的讲台,参与到文学生产的第一线。
作为编辑兼作家,在与不同作家的交流中,陈崇正获益良多,他还专门设了一排书柜,拿来放朋友们的签名赠书,其中大部分是广东青年作家,包括王威廉、林培源、陈培浩、李德南、唐诗人、冯娜、郑焕钊等等。陈崇正说,这几年广东作家势头很猛,尤其是这一波80后、90后青年作家,保持很良好的态势,“写作是一条非常非常孤独的路,我很荣幸能有这些优秀的朋友作伴。”
【访谈】
南都:金庸对你有何文学意义上的影响?
陈崇正:相比外国文学,我的写作应该是从中国作家那里获益更多。小时候,我在一个乡村长大,村里其实没有很多书。因为家里老一辈有行医的,所以还有一些医学藏书,里面关于穴位的图案,当时对我来说很神秘,很有趣,一方面又影响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当我再去读金庸的时候,我接受起来非常顺畅,金庸小说里涉及到的穴位、五行、八卦,那时我都已经很熟悉了。
有一段时间我对金庸是非常痴迷。对一个乡村少年来说,金庸的小说为我提供了许多成长所必须的精神营养,其中有中国文化,有情感模式,还有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讲故事的方法,“原来还有一种小说这么狂野”,它有非常疯狂的想象,一个乡村少年的英雄梦就被激发起来,同时,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深影响我,至今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深深受益。
南都:同时作为一个潮汕人,潮汕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文化。
陈崇正:我在潮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但其实我一直在跟潮州的文化保持距离,我一直努力地从这一切我所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抽身出来。但是,等到人到中年才慢慢发现,自己身上的潮汕文化因素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它已经深深影响了我,比如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早上起来我会喜欢先冲一杯功夫茶,这样一个生活习惯我之前没有觉察。潮汕文化既传统又封闭,就像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的标本,我是在这个标本里泡了很久,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南都: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你的小说还有一股先锋的气韵,曾被邱华栋评价为“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附身”,你怎么理解?
陈崇正:邱华栋老师应该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作品中的先锋性,才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谈到先锋气韵,还必须从我的阅读说起。刚才我们谈到金庸,金庸的小说深深影响了我的想象力。我天然地抵制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作品,这是一种个人的审美取向。特别在我遇到王小波之后,我更坚定内心的判断。在王小波那里,他告诉我,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思维操练。
我沿着王小波的步伐慢慢打开了对更广阔的西方文学的认识。他喜欢卡尔维诺,我就一下子读完“祖先三部曲”,如果喜欢一个作家,就跟随他的脚步,这也许是一条省力的道路,但是,当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的文字语感上跟王小波很像,我意识到是时候应该挣脱王小波对我的影响,而且一定要挣脱。一个老师带你入门,但是你不能成为他,如果被人说你是第二个王小波,第二个莫言,第二个余华,第二个苏童,那意味着你是失败的。所以我不断在探索文学的先锋表达,才会写出“变形三部曲”:《分身术》《折叠术》,还有尚未出版的《悬浮术》。
南都: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你买书的时候会留意一本书的哪些方面?
陈崇正:文学编辑逛书店,关注的东西就多了,除了看书的内容,还会留意装帧、定价、目录编排,甚至留意不同的书在书店里摆放的位置,有什么特别的营销手段等等。不过,现在逛书店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是在网络上逛书店,网络上经常会有图书打折,但米贱伤农,其实对出版行业和写作者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南都:你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陈崇正:我可以说是一个散漫的读书人。在我看来,所有的书无非是读书人的玩具。没有必要把图书神圣化,它就是用来阅读的。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新书刚买回很激动,觉得要翻一下,要看一下,但没读完就放起来了,就像一个玩具一样。其实也不必太认真,如果不做学问,随意的阅读是很愉悦的。反正就随手翻翻,有些感触了,就记录下来。翻得多了,你就会看到,原来这一个作家曾经这么思考问题,那一个作家曾经那样讲故事,这些作家曾经把故事讲得这么漂亮,还有人能把句子写得这么好……所以,读书也是玩书。新的玩具玩腻了,回头看看老的玩具也不错,读一些前辈作家,就会反思:我们当下很多写作,真的比几十年前的写作更进步吗?有时候也不见得,有时候是停滞不前,甚至有时候是后撤的。你当下读到一个很新颖的笔法,也许隔一些年回头看会发现,其实你所认为的新颖,所认为的创新,也是相对的。
南都:未来有没有全职写作的打算?
陈崇正: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全职专业写作,但是不太现实。对我来说,当文学编辑已经是对写作伤害最小的一种职业了,毕竟还是跟文学息息相关,不会像其他职业有那么巨大的冲突。
我并不主张一个作家完全变成职业作家,尤其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社会阅历很重要,同时有一份工作,有一个社会身份,不管是教师、律师,甚至是一个厨师也好,你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受到社会边缘的颤动。那些角落里的人物如何生活,是写作很重要的视野和角度。像我当文学编辑,至少知道有一些稿子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少我不断在跟中国最前沿的作家交流,这些交流很重要。写作中有一些波动暗涌是具有方向性的东西,文学思潮正是在每个个体的创作中汇聚到一起最后形成的。
比如说最近许多严肃作家写科幻题材,关注未来,关注AI的话题,像这样一些热潮是暗暗涌动的。作家们突然意识到应该关注未来,关心人类,反映了作家们的共同思考,这些思考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得出结论和判断。作家很难完全挣脱职业的束缚,但是职业的束缚有时候也会提供另外的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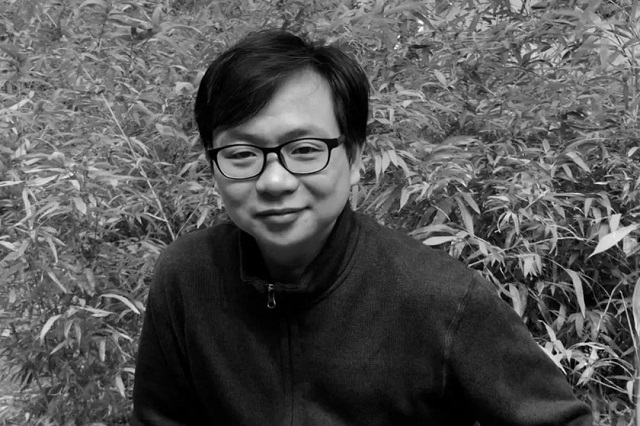
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著有《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入读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硕士研究生班;现供职于花城出版社《花城》编辑部,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