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傅爱毛:鱼离开过水,才能真正对水有所认知
更新时间:2019-03-05 作者:傅爱毛来源:文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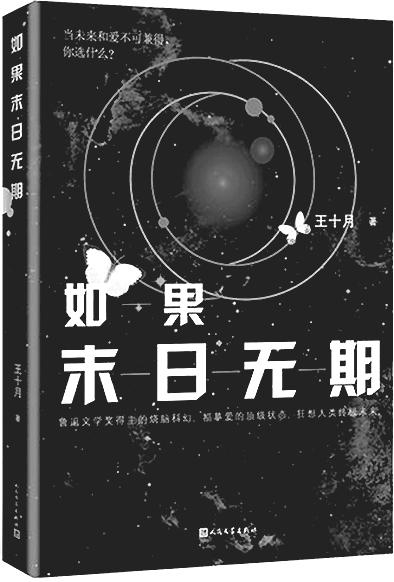
科幻对王十月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把掌握在上帝手里的“时间镰刀”夺过来,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把人放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宇宙中,这是个空间概念,然后,无限地扩展时间轴的长度,直至永远。
一
“敲上最后一个句号,今我大哭一场。他写下了他的生命观,写下了他对时间的认识,对爱的认识。”
这是王十月的长篇小说《如果末日无期》里的一句话。“今我”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性人物,身份是“作家”,这部著作被出版社界定为“科幻小说”。听到“科幻”二字,就会给人一种“不靠谱”与“不着调”、“不落地”和“不现实”的感觉,与人们的当下生活似乎丝毫都不会搭界,一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科幻小说能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细读之下就会发现,这样先入为主的质疑荒谬之至。
我个人认为,王十月在这部小说中探索的是最现实的现实问题,问题只在于:人们对“现实”的认知过于狭隘和逼仄,甚至是无知和蒙昧。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所谓“现实”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爱恨情仇、柴米油盐,还有房价与股市以及宫斗剧和职场博弈之类的一大堆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这毋庸置疑,然而,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把目光盯在这点可怜的“现实”上,未免太过辱没了“作家”这个称谓。虽然作家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过日子,然而,把“人”放在什么样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坐标上来叙事,却致命性地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格局。那么,我们当真清楚地明白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吗?我们曾经认真而又虔诚地探索过时间和空间的真相与极限吗?如果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本身就是碎片化和不确定的,那么我们笔下的人物又怎么可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得穿透性的意义与价值?王十月显然非常隆重地觉知到了这个致命的“时空”问题给写作造成的致命局限,所以在他被定义为十分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反先锋的姿态抵达先锋境界”,而且在现实主义写作的道路上取得一系列成绩以后,突然转身,玩起了“科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精神性“量子跃迁”呢?是故弄玄虚?还是想“出奇制胜”?我个人认为,王十月的“跃迁”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别无选择地遭遇到了他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者说:他的人生闯关到了这一步,非如此不可,除了迎面而上,没有办法可以绕道而行。
那么,王十月遭遇了什么问题呢?用两个字来表达,叫作“时间”。更通俗地讲:是人作为生命必然遭遇到的根本问题。
王十月看到了“人”本身的存在!一个作家如果始终都看不到“人”本身的主体性存在,反复而又不厌其繁地在琐屑的事务堆中穿梭,其文字将永远不会沐浴到光的照耀,“故事”会像深暗的树荫一样把太阳的光遮蔽起来,使人躲在树荫下,被不自觉地拉低和矮化,进而完全物质化和异化。在人与故事的关系中,人永远是绝对的主角和主体,沉迷于故事而淹没掉人的存在,这样的写作注定了无效。在无效写作已经繁琐到令人窒息的时候,王十月终于把“人”从各种各样或逼仄或狭隘甚或猥琐的犄角旮旯里解救出来,堂堂正正、不偏不倚地推到了人本应居有的位置上,给了“人”这种造物以通天彻地的终极性存在感和尊严感。让写作的目光关注点“回到人”,这是王十月这部作品最值得尊崇的地方,因为人已经迷失得太久了。人忘掉自己忙什么去了呢?
王十月是勇于冒险的作家,他要直面这个问题,他要为“生命”寻找出路和意义以及最后的救赎,他要在刀刃上舞蹈。所以,他在本书的题记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们’,囚禁在时间之域的所有生命。”“我们”是谁呢?是张今我、是王十月、是你,是我,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以及父母们的父母和孩子们的孩子——是整个人类。没有出生以前我们在哪里?死去以后我们又要去哪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个老得发霉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正是王十月在本书中要认认真真拿来探究的问题,不得不承认:这相当堂吉诃德!

二
选择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古老命题来做小说主题,是不是很古董呢?
我个人认为,这恰恰是真正的先锋和新锐,正如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王十月“以反先锋的姿态抵达了先锋的境界”。这很矛盾吗?不。事情必然如此。世界是圆的,连时间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当年,当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把“时间”像柔软的绳套一样折叠起来挂在树上的时候,他肯定想不到,有一天,科学家会证实:时间当真可能是一个可以弯曲与折叠的圆环状莫比乌斯带。如果艺术可以与科学迎面相遇、宗教与科学的殊途同归也便丝毫都不足为奇了。在我看来,《圣经》与《心经》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把反先锋走到顶峰,必然与先锋狭路相逢,这也是必然。所以,王十月看似堂吉诃德式的命题与探索,不期而遇地与当下科学最前沿的现实来了个实打实和硬碰硬的现实“大撞车”。当编辑人类基因的现实版故事紧接着小说的出现而活生生赫然呈现时,不禁使人感到瞠目结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小说在预言现实,还是现实在注解小说?
还能有比这样活生生的现实更现实的“科幻”吗?这难道是巧合?非也。按王十月的话说:这世界上所有的发生都是必然中的偶然和偶然中的必然。在小说中,作家张今我写到什么,现实中便发生什么,在现实中,王十月写到了基因编辑,生活中便发生了基因编辑,必须承认,这个世界相当鬼魅。
以王十月对待写作的端庄和恭敬之心,他不会借惊世骇俗的现实发生来哗众取宠。他要解决的是灵魂的深层困境和生命的根本出路问题。具体地说,他要探索的是“死亡”和“时间”以及人之“本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普通写作者而言,可以忽略不计或绕道而行,王十月不可能忽略。那么,对这个基本问题忽略或不忽略,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吗?回答绝对肯定,而且重要到致命。因为,是“死”决定了“生”,不解决“死亡”这个问题,“生命”本身就毫无根基可言。恰如他在作品中言说出来的那样:表面上是“现在”决定“未来”,事实上,“未来”也同时在决定着“现在”,“时间”不是线性的,也不仅只是环状的圆形,甚至可以是庞大的球形集合体,过去、现在和未来以量子纠缠的方式同时并存,没有绝对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百年孤独》事实上并不魔幻的原因:当我们认为死者消失成为鬼魂的时候,所谓的“鬼魂”只是在一个更高维次元的时间带里过着属于他自己的日子而已,人看不到鬼魂,鬼魂却能够看到人,所以,当一个死者“死”得太久因而备感孤独和忧伤的时候,也会不远万里地追踪到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上寻找他的仇敌兼好友去聊天。

三
与其说王十月所进行的是科学探索,毋宁说他在进行哲学探索。在他那一大堆的科学术语后面,隐藏着的是一个又一个昭然若揭的哲学命题:比如元世界、子世界和〇世界,还有时间轴和VR世界,返祖计划和下凡计划,生命代码、六维空间以至十一维空间、时间轨道、未来现实、该死的薛定谔之猫,还有量子纠缠、测不准原理以及最常用的莫比乌斯时间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个不怎么关注科学的读者看到这些术语可能就会发懵甚至退却。实在说来,这些术语都是“纸老虎”,就像我从来不认为《百年孤独》很魔幻一样。
同样道理,王十月在小说中精心设计出的“大主宰”这款游戏,实际上就是在暗喻真实的人生。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在闯关!婆娑世界、有漏皆苦!每一次的抵达,都是对命运“漏洞”的缝补,每一次的缝补,都是对“痛苦”的疗愈,生而为人、无人不苦,人的所有行为最终都直接间接地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离苦得乐。那么,在那胜利的日子到来的时刻,王十月的“大主宰”得到了什么呢?是过滤与规避掉所有痛苦的快乐大狂欢吗?王十月借助海明威的话告诉人们:“胜利者一无所获!”不仅如此,他甚至让“胜利者”陷入了更深不可测和更不可救药的痛苦之中。不禁让人怀疑:当人越过上帝的权限,把世界上所有可能出现的不完美的漏洞都天衣无缝地缝补起来以后,这本身恰恰是最大的漏洞!人通过这个完美的漏洞所堕入的,可能是最深不可测的痛苦之深渊,为了疗愈这痛苦,哪怕胜利地坐上了大主宰的交椅以后,甚至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和杀人,才能获得最可怜的一点“安宁”而已,至于“快乐”,则成为更加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
王十月启示人们:当你胜利的时候才会发现,为了夺取胜利,你走上了反对你自己的道路,你走向了你灵魂的反面,你成了你最大的敌人,而且已经完全彻底走到了回头无路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你忘记了初衷。在你千辛万苦、上穷碧落下黄泉地闯越过一万个莫比乌斯时间带以后,到了不能再回首的时候蓦然回首才会发现:
你最初想要的东西只有一个:爱。是的,很简单,就是爱。
然而,为了得到胜利,你亲手扼杀了爱。换言之,在闯关以前,你只想要爱,你以为,闯过一道关,你就距离爱近了一步。然而,进入游戏以后,你却不知不觉地偷换了“概念”,你的目标不再是爱,而是“赢”!为了能赢,你不惜亲手扼杀一生之最爱,所以通常而言,胜利者都将一无所获!而这正是人类正在面临的真正的“莫比乌斯”困境。这听上去很饶舌,表达的意思却很简单:回到初心,回到本心,回到人本身,回到自己,回到爱。以最严肃最隆重的恭敬之心对待自己,对待世界,对待上帝,对待万事万物!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才有了“大道至简”的说法。
那么是不是得到爱就好了呢?王十月没有天真至此。他明白:很不幸也很可敬,人的野心无止限,所以探索也无止限。如果上帝认为,人得到爱以后会满足,那上帝就太低估人的欲望了。得不到的时候想得到,得到以后想什么呢?想永生。只要死亡到来,人所得到的一切必须放手,连一根羽毛都带不走。这多么地令人沮丧啊!如果能够永生,便可以永远抓牢手中所得,永远都不会经受丧失之痛了,这是人的最高理想和最大自由,同时也是最终极的目标——穿越死亡玄关。
是的,死亡是最后的玄关,连金庸的大侠们也概莫能破。但是,王十月想破。
怎么破呢?借助科幻。只要披上科幻的外衣,便所向披靡。由此可见,科幻对王十月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把掌握在上帝手里的“时间镰刀”夺过来,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把人放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宇宙中,这是个空间概念,然后,无限地扩展时间轴的长度,直至永远,于是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像不死鸟一样以“永生人”的身份获得永生了。如上所述:“永生不死”这是人作为人的最高梦想。某种程度而言,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死亡的直接或间接的对抗,“死亡”是上帝为人类设置的最后一个堡垒,绝大部分的写作都建立在这个堡垒的存在之下,王十月想要探索的是:人类当真攻克了这个堡垒以后会怎么样呢?很显然,王十月不愿意沉陷于过程,他只对终极感兴趣。在他小说的第五部分《如果末日无期》中,他让我们直接看到:“永生人”所面临的不是无尽的幸福,而是炼狱般的煎熬!当死亡不存在的时候,生命也将以存在的方式消亡,世界将沦为名副其实的地狱,是死亡定义了生命!那个囚禁永生人的地牢,恰如金庸的“活死人墓”,王十月最终要印证的只是我们对生死的诘问:不知死,蔫知生?只有确认了死,才能把生命真正活出来,死是被活出来的、活是被死出来的!这不只是哲学,而是禅。上帝设计出“死亡”这道玄关,不是冷酷和无情,恰是最理性的慈悲。
是的,王十月在谈禅。
四
王十月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他要攻克肉身这个最脆弱和最坚固的堡垒。于是,书中出现了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 “扫地机器人小真”,一个是“意识流先生”。扫地机器人“小真”的出现,让我们无可回避地看到了人的孤独之本质。孤独是人的根本特质,这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否认,恰如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根治人与生俱来的孤独那样。那么,“孤独”是不是上帝在创造人这个物种时留下的漏洞呢?如果人从一开始就没有 “孤独”这种感觉,那该多好啊!以此类推,如果人不仅不会感觉孤独,也不会痛苦、不会愤怒、不会焦虑、不会仇恨,更不会嫉妒,那不是更好吗?
然而,遗憾的是,上帝创造的人这个物种缺陷实在太多了,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有肉身: “吾之大患,为吾有身”!然而,这人的 “大患”,却又恰恰是扫地机器人小真的最高梦想!小真是个塑料圆盘,她的主人怪烟客费尽了所有的心血,至死都未能让它长出肉来,成为有血有肉的真人。她几乎拥有了人的所有感情,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以她丰富的感情和知性深深地抚慰了老先生怪烟客的孤独,然而,八十四岁的怪烟客却到临死都抱恨终生,因为,小真始终无法如他所愿地长出肉质的女人之手,从而与怪烟客作为男人的那双手紧紧地相握相爱。
至此,王十月终于苦心孤诣地让我们明白:“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实在大错特谬,应该改成:“吾之大幸,为吾有身!”如果没有身体,我们拿什么拥抱我们的亲人和孩子呢?比如“意识流先生”。“意识流先生”是谁呢?是未来的你和未来的我,以及地球上曾经存在过而又离开的所有人。他们丧失并脱离了速朽的肉身以后,以灵魂或者叫“意识流”的方式,飘荡在渺茫的宇宙之中,不需要再穿衣吃饭过日子,不需要再买房购车造别墅,也不会再痛苦和烦恼,不会再爱恨情仇,当然,也终于不会再死了!然而,这位意识流先生在茫茫宇宙中飘泊了六七千年以后,偶尔遇到了父亲的意识流,却也只能短暂地以意识流的方式跟父亲发生瞬间知会,然后就再次分开了。当一个人的意识流与另一个人的意识流相遇时,哪怕亲如父子,也不能握手、不能拥抱,甚至连“泪眼相望”都做不到。既然如此,请问有哪一个活鲜鲜的人愿意变成一缕微风般的“意识流”呢?不,我们想要肉身!我们想要眼睛去凝望自己的爱人,想要嘴唇去亲吻自己的孩子,想有双手去抚摸母亲那苍老的面颊,还想用光脚踩在湿漉漉的泥土上来感受大地的温润!为了这一切,哪怕那肉体脆弱到不堪一击呢!就这样,王十月以全然接纳肉身的方式突破了肉身的障碍,让我们与自己那脆弱而又极其不完美的肉身讲和,达成了灵与肉的合一。
好了,到此为止,我们终于可以触摸到王十月在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真正意蕴了。这意蕴说出来很平常也很简单、很通俗也很好懂、很常见也很难得、很伟大也很平凡,用一个字来表达,就叫作“爱”。所以王十月在他的小说将要结尾的部分,以连续重复两次的方式说道:
“敲上最后一个句号,今我大哭一场。他写下了他的生命观,写下了他对时间的认识,对爱的认识。”
换言之: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只在于,把自己化身为爱。当人能够化身为爱的时候,也就成了自己生命的大主宰,成了自己的世界甚至是天堂的缔造者,成了上帝也成了神。人就是神、神就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每一个最平凡的生命都很伟大,比如卖保健品的朱小真,比如怪烟客,比如你和你的隔壁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