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梁凤莲 | 《应愿之地》
更新时间:2017-10-12 来源:广东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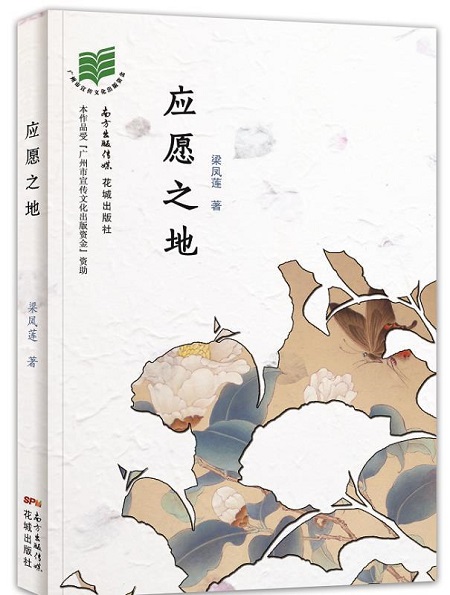
书名:应愿之地
书号:978-7-5360-7939-7
定价:30.00元
出版时间:201606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散文集,梁凤莲将对于广州的关注与思考,在寻常生活的体验中,坦诚地注视生活广州的时间和空间,真诚地注视涵蕴其中的文化与历史,拓展视野,走向世界,探寻城市独特的魅力与韵味,她用擅长的文学表达方式,来歌颂她热爱的家园,歌颂生活及生命。
作者简介:梁凤莲,女,广州人,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系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广州市优秀专家、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等。为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共出版个人著作32部,其中文化研究与文艺评论专著16部,代表作有《乱云飞渡——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之途》《容度之间——岭南文化与文学的内省及互证》《城市的拼图--广州市各区文化品牌研究》等;文学创作专集16部,代表作有长篇系列小说《羊城烟雨》、《西关小姐》《东山大少》、散文专集《应愿之地》《广州散韵》等。
梁凤莲的广州情绪及其新女性主义写作
陈娃
翻阅《应愿之地》的书稿,一股老广州的人间烟火味扑面而来,梁凤莲气息的“那些广州――那些绵密曼妙的街巷;那些迤逦成片的骑楼;那些街巷里的曲折与衷肠;那些心念所属的治疗;那些靓汤好茶里神奇的精灵与蝶变;那些食肆店铺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临水听声的世俗……”一篇一篇,一瓣一瓣,如同长风浩荡下的紫荆花缓缓飘落,具象为一幅幅古雅风俗的版画,白玉兰的香味,麻石街小巷的叫卖声,珠江水面飘来红线女的粤曲《卖荔枝》…渐次铺展在眼前、鼻尖和耳畔,让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有那么瞬间,我觉得眼眶忽然潮湿,好像失落已久的“故乡”回来了,在时光与空间之外,乡愁像一只会变色的蜂鸟,在我跟前流转鸣唱。坚持以岭南立场来写作广东和广州的作家,应该有一些,对于这群人,无论熟悉或者陌生,我都想要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而其中我阅读得比较仔细的,对文本印象又比较深刻的人,男作家当属叶曙明,女作家就是梁凤莲。
“那时广州的骑楼,就如同那时时兴的旗袍或者大襟衫的镶边,顺着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缠绕,其绮丽婉转,一如滚边沿着旗袍曼妙的曲线,在城区房舍的铺摊中婀娜延展,勾划出广州一格成韵的风情,而这风韵与风情正是由这些别致的建筑牵手组成的音符,使得广州的城观有了不一样的情调与韵律。而且,还仿如那时中老年女性的大襟衫,把连袂成片的横街窄巷簇拥在衣衫的宽大里,从外表的端庄雅致到内里的琐碎热闹,亦如从骑楼转入小街小巷,就是地道浓郁的市井营生,该有的人生百态该有的日子滋味都在其中了。”
――梁凤莲:《那些迤逦成片的骑楼》
骑楼,是广州传统市井文明的一抹重彩,在梁凤莲的浓墨勾画之下,它们“该有的人生百态该有的日子滋味都在其中了”。《应愿之地》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一股刻着时代烙印的“广州情绪”。英国女占星师莉娅.怀特豪斯最近撰文说:“…你只需要看着海洋是如何拍打陆地的,就会明白情绪对你的塑造模式…” “情绪”对人的塑造毋庸置疑,对作家文本的塑造也是一样,梁凤莲写作中有种广州情绪,张爱玲写作中有种上海情绪,“情绪 ”在这里成为了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共通的东西,而不同的“情绪”产生了不同的作家形态和文本个性。“情绪”是灵魂与肉体相依交战的分泌物,不是完全的感性,也不是纯然理性,它一定是感性和理性的水乳交融。梁凤莲散文中的这种“情绪”,可以说是我熟知的,日常得好像我们促膝而坐,话家常,吃点心,互赠女伴间才拿得出手的礼物……
飘到东,飘到西,穿行在浑沌与无着、浮躁与尘埃之间,惶恐地度过虚无的每一天,连惆怅地回头和张望都顾不上,怀旧也变得分外遥远及奢侈,成为了一种不可企及的“诗意”。而梁凤莲和她的《应愿之地》,于我是一种温柔而伤感的唤醒,复活了我沉寂已久的广州记忆。1994年,梁凤莲作为广东省作家协会首位签约作家,名声大噪,她的才子佳人式的文学婚礼更是轰动一时。我还记得,在婚礼前夕,凤莲姐姐吩咐我们这些文学圈的小弟妹们帮忙布置现场,一会指挥我在窗前插花,一会叫黄礼孩在墙上贴字……
我那时每天往返童心路上班,集采编于一身。在《广州之声.屏幕之友》头版,我刊发过一则凤莲伉俪婚礼的图文。二十多载春与秋,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问她,你还记得么?凤莲说,哈?真的吗?我都没那期的报纸…你们采访的都是大明星,你也没告诉我说要把我也登上去呀……说到这里,我们大笑,笑声中隐约可闻当年的纯真。凤莲说的不错,当时的广州电台(兼广州电视台)台长叶小帆,是一位高知文化女性,浑身的活力、能力和魄力,锐意进取、创新和改革,有许多开国内之先河的举措,《广州之声.屏幕之友》主编是潘健生,也是一位知名诗人,虽非大报,却是一份颇有“八卦”份量的文化娱乐报纸,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著名音乐、音像等机构和明星的注目,包括一些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风云人物,与文学的交感确实不大,但由于我这个文学青年与文学的关联,我将这份报纸寄赠给广州及国内外的作协和文友,因此知道它的人也不少,也有文友写些评论性文字给我,我也一律照登,甚至刊发过几次诗歌。那些在童心路度过的青葱岁月,像一股温暖又陈旧的海风,不经意地掀开记忆的窗帘,带给我曾经苍海的慨叹,却也没想到,帮我重温旧事的人,竟然又是凤莲姐姐。
在阅读《应愿之地》的过程中,我头脑中跳出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字眼,因此自作主张将梁凤莲散文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没有征得任何批评家的同意,也没有跟凤莲有过商榷,但确实有我的道理。
以我的个体阅读观察和文学直觉,当代散文令人诟病的地方不少,技艺上的创新几乎也陷于停滞。我笼统地以自己的方式分成几大类:文化大散文;小女人散文;心灵鸡汤散文;各种艺术随笔等。有些被推崇的包罗万象的大框架散文,无论题材视野,到谋篇布局,都显得巨大空灵,让人屏住呼吸来读,虽则郑重其事,却像端着一把椅子在罚站,不给坐下去,失却了自然意境,平常心态。再说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小女人散文,在一个日新月异、暴风骤雨的大时代,个体的情绪、感受、甚至于命运遭际、以及生命本身,在风驰电掣的时代列车滚滚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卑微,好比草芥渺小,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活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是每个人都遭遇到的严峻拷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小女人散文还是小男人散文(假设有小男人散文的话),都是对“个体”――“单独的人性”的一种重视,一种释放,是对个人生命意志的一种具体的抒发,它喊出了“我”的声音,“我”很重要,说出了女子(或男子)作为一种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独特感受,强调了女性(或男性)在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存在感――不管从“人”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具有十分积极的进步意义。
因此必须承认,小女人散文曾是中国女性主义散文写作的一个显著标本。然而,曾几何时,那些流淌在风气中的小女人散文,渐渐充溢一种娇弱绵软苍白无力的“小女人情绪”,总体上表现得像一枚灵魂干涸、情欲旺盛的花蝴蝶――不但题材上狭隘,内涵也单调单薄,至于社会道义层面更加无所担当,除了虚荣心,别无痛苦,除却男女之情,别无他爱;好像时刻都在以一个未成年女子的心态向生活撒娇、索求……这种写作,虽然是女性意识的写作,呈现喜怒哀乐的方式莫不出自女性手法,但本质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写作”。这是极端的“女性”泛滥,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单纯从文学的角度,这种对“性别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强调,本能地排斥了女人的“妻性”,特别是,根本不具备女人的“母性”,更别谈及世俗意义的日常化的“主妇性”……“妻性”、“母性”以及“主妇性”,可能不必要解释,我想说一下的是,什么是“女性”――我个人将它定义为:性别的本能之一,极端亢奋的“女性”情感和意识,在此必须以“男性”作为在场者和参照者,用最通俗的话来比喻,就是不分场合,见了男性就会本能地“撒娇”,本能地演示自己的性感魅力,本能地要求男性将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本能地要“争风吃醋”;再比方说,一个满脑子爱情梦幻的女人,哪怕活到四、五十岁,孩子生了几个,她也是很少母性的,这也是“能量守衡”的表现,伴随着过度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她的丈夫或情人或许在情爱上是满足的(同时也有可能因她的频繁出轨而嫉妒发疯),然而她的孩子却有可能感到缺失母爱……在真实的生活中,极强烈的“女性”会引发冲突和矛盾,产生分歧和犯罪;在文学的情境中,极端极致化的“女性”意识虽不至于引发危险,但却可能失却构建文字世界的风度、从容和达观,无法彰显人性的圆融和成熟。
在生活中我也留意到,极强烈的“女性”是不分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或出身背景的,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1世纪的2016年,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作为参照,仍有一些很“女权”的女性,一方面要“极度掌控”,一方面要“绝对依赖”,体现出极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情感特征,这本身是矛盾的,也是有趣的,这种现象是女性性别自我发展的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值得人类学家考究。我记得作家马长山许多年前说过一番话,大意如此:给女士开门、让座,是尊重女性的表现,不给女士开门、让座,是尊重女权的表现……两者果真是不可调和吗?其实也未必。在写作中,也正是由于缺乏了一种将女人的“女性”、“妻性”、“母性”以及“主妇性”揉和搅拌在一起的“中和性”或者说“包容性”,由于缺乏了一种大生活背景的阅历和淬炼,由于缺乏了一种大博爱的情怀和悲悯,只有对自我的关爱和怜惜,没有对他者的同理和同情,只要求外界和“男性”的共鸣,却没有交付出对生活以及对“男性”的基本共鸣,不自觉地形成了极端女性情感特征的性别中心主义,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据我观察,至今没有引起写作者与批评界的注意,凡此种种,构成了女性主义散文写作的局限性,使许多文本成为一种肤浅的泛抒情;极端女性情绪的过分流露和放任,客观上削弱了女性主义写作的理性思维和包容意识,而且在写法上、文字上,也不见得有太多惊喜,谈不上艺术的突破,反而相映成拙,越是强调女性立场的写作,越不具备女性的天然禀赋和美学,天高地阔更显胸襟之窄陋,对于讲究一点的、境界高远一点的阅读者来说,会感到乏味和无趣,产生很多质疑和不认同感,失去对文学的尊重。如果散文写作者眼界不提升,性格不成长,而将初级阶段的女性主义写作视为日常、正常,甚至于在某些批评家的文本下变成“惊艳并伟大着”,这是对阅读者思考力和理解力的一种蔑视,也对中国当代散文的自我建设与创造产生负能量影响。
同样是女性主义散文写作,梁凤莲散文中的女性情绪流露却并不极端和刻意,不但不极端,而且很温婉,很善良,有时甚至很谦卑,忍让到令人心疼的地步,没有一种对男性话语权色厉内荏的指责,没有咄咄逼人的强势――而你也完全不必担心,这样的女性写作是“不平等”的。恰好相反,我觉得这样平和的“女性情绪”才应该是常识化和常态化的,这跟凤莲平时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比较吻合,她实在很客气,很有礼数,很重视别人的感受,从不流露出贡高我慢的心态。凤莲是贤妻良母,有一个安乐的家庭,是一个处女星座的好主妇,非常讲究完美,家里的每一寸地板都擦拭得光洁如新,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的女性写作情绪的节制和内敛,固然跟她“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家庭观念有关,也跟她的“学者”思维同样脱不开关系。身为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市优秀专家、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等等头衔的梁凤莲,著作等身,载誉无数,共出版学术及文学个人著作28部,其中文学代表作有长篇系列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巷娈》,散文集《被命运催赶的夜晚》、《远去的诺言》、《广州散韵——相遇或者错过》、《广州散韵——情语或者诺言》等等。她是暨南大学文学与文化博士,后来又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进行博士后的研究,这样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广东省,甚至在中国文学界,就她的高学历而言,确实令人瞩目,然而,她的才识、女性定位、性情操守以及学者型包容性思维对她的写作产生的影响,则更值得引起关注,这使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具有了相对的超越性与独特性。这本以女性心态、学者胸怀、赤子情绪交织而成的《应愿之地》,是女学者厚积薄发的心语倾诉,是向一座城市致以敬爱的深情表达,既有原汁原味的生活积累,又有历史追问以及人性思辩,呈现出一种女性主义写作的深广度。文字当中有一种反思力,不但关爱“我”,怜惜“我”,更关爱“我们”,怜惜“我们”,这个“我们”,并不只是“同性”,还有“异性”,以此构成了女性写作的“包容性”。我感到她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觉醒、超越和创新,她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出发,但又越过了自己的小宇宙,将视野投放在无边无际的现实世界里,也同时向无始无终的哲学精神领域伸延。从一个女人的文学状态,可以观照她的生命状态,从一个女人的写作姿态,也可以洞见她的日常生活。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二十年中,梁凤莲早已经开始了她的女性性别成长的个体跋涉,不以性别抱屈,也不以性别自傲,她抛开了性别的困扰,终于做到了把自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开发和探索,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磨砺和完善,以此方式,她竟完成了女性性别成长和女性主义写作拓展的双重提升――感知到这一点,我很是惊喜,无论梁凤莲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也都意味着她开始了一种新女性主义的文本写作,不再重复别人,也不再重复自己,正如毕加索所说――世界期待我们去创造,而不是重复。新女性主义写作能挖掘到什么宝藏,是否能将中国女性性别成长的空间和容量真正拓宽,仍需要拭目以待。
现在再回头看看作家马长山提出的“女性”与“女权”的有趣比方,两者到底怎么调和,这当然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两性差异”。男女两性是有天然生理差别的,从婴胎期的染色体差别开始,在构造、体态、体能、声音等方面的差异都是明显的,这种差异很可能会造成情感表达、心智发育、思维方式、兴趣爱好、职业选择等各种各样的差别。我们一直强调的“两性平等”,原是指社会地位和精神意义上的平等,如果方方面面都要求一律平等,也是有违常识的。1910年8月,在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倡议下成立三.八国际妇女节,次年开始正式施行,当然有一定政治色彩。后来德国有女权主义者提出异议说,70年代我们不再(需要)有妇女节了。话虽如此,在七、八十年代,德国接连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维护妇女权益,自此以后,在街头抛掷廉价的文胸、内裤之类的妇女节游行活动日渐式微。所以,妇女节在德国起源,却并不在德国持续地喧嚣。再后来,大概是2000年底,我在汉堡读到了《Emma》(《爱玛》)杂志,之后订阅了多年。创办人艾丽丝.史娃泽是德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杂志里面的文章许多都由女性主义作家书写,我也不觉得她们在观点或内容上有过度自恋的“女性”主张。艾丽丝.史娃泽在2010年发表观点说,妇女节是社会主义式的母亲节。从“妇女节”到“母亲节”,这是内涵全新的定义;“母亲”与“妇女”之间,有从属的亲缘关联,前者却更具体,更有职能感和社会性,这是一种传统角色的回归,是不是也在呼唤妇女们焕发和回归她们的“母性”呢?这个只是我的私人揣测。但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用我的所见所闻证明,德国女士们在总体的性格方面都趋向于“中性”、“主妇性”和“母性”,一般都不愿意更不习惯开发“性别资源”,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们在精神层面上早就已经实现了“两性平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有独立心,作为一个“社会人”有平等心,作为一种“性别”有自尊心,她们是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女性”,也是真正强大的“女性”,“政治家默克尔夫人”不知道算不算有说服力?我在德国时,曾就默克尔夫人当时的衣着过于“古板严肃”发表过看法(当时的默克尔夫人正在积极竞选),登在欧华导报上,而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男人)大致是这样对我说的:默克尔夫人是科学家,又不是明星,用不着穿得花枝招展的…所以,中国男性作家马长山的“应该给女士让座还是不让座”的纠结,对于德国男性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德国的女士们根本不在乎男士们让不让座,如果你在妇女节这天,要求一位男士对一位女士说“三八快乐”,恐怕双方都会尴尬不已。
无论中国的人文环境有多少特殊性,女性成为“母亲”,男性成为“父亲”,这种两性自然分工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不妨承认差异,却大可不必过分去强调差异。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与男性是友爱的,真正的女性主义写作,与男权话语也并不意味着剧烈冲突。男女两性的性别发展是相辅相承的,两性的成长依赖于互相促进彼此启发,这也决定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成长,需要男性的共同成长作为伴随。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曲折发展,折射出当代中国男性的心智成长度和个性成熟度,而两性成长的契合度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人性发展的总成熟度。从世界文学的大生态来说,光有男人在写作,光有男人话语的文学,或光有女性主义写作,光有女性意识的笼罩,都必然会导致阴阳失衡―― 一个精神健旺、饱满有序的文学时空,是两性共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深刻又丰富的人性共鸣结晶体。
写到这里,想起藏传佛教家希阿荣博堪布曾这样说过“人”和“人性”:“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塑造者和负荷者。关于一个时代的劫运,其实无须问别人,看看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行动就能知道。共同的因缘,唯有大家一起在思想、行动上改正、进化,才能慢慢扭转。解铃还须系铃人。”――不以出家出世、与世无争为理由来回避“时代与人”,也许对当代的文学、文人、文本,也是一种开示。
我以前也写诗歌,写散文,现在主要是写作小说,有时也写点博客文章。作为一个散漫的自由写作者,并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或流派,也没有刻意去考究人性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然而事实却又证明,人性与文学一直在互相交汇,互相影响,互通有无。文学就是人学,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这句话具有永恒的意味。我旅居德国多年,自从数年前回归家国乡土,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有不少文学发小已经名满天下,见面也偶生隔膜之感,不复当年的亲爱热诚。只有凤莲还是如常的亲切,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那十年,好像我从没有去国离乡,一直都在,我们彼此在精神生活中仿佛有着从不间断的沟通……我有时很感触,我大概――或许――甚至肯定――也成为了梁凤莲广州情绪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吧?一波涟漪?一次瞬间?或一个原生态的符号?所以她才会如此地善待于我?每次评论家协会年会散会后,还没等我回到家,她的电话就打来了,她说人多没有跟我好好地说说话,因此在电话中,我们常常一说又是半小时,电话这端和那端的人,都在抢着讲话,凤莲有时会幽幽地叹息道:唉,打电话跟我争着讲话的人,就是你啦。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一隅,凤莲诚恳地邀请甚至是“央求”我去她家做客,去啦,去啦,我给你煮马来西亚咖啡哦――在这个人与人通联方式最丰富、人与人距离却最遥远的后互联网及新智能时代,人们宁可与机器人为伴、与AlphaGo对弈、也没有信心与兴趣跟人交流的时代,在人声鼎沸的大广州城,一个明明忙得不可开交的、社会活动繁多的广州文化名媛,却抱着最真实的初心请朋友上家里去聊天,这样的人和事应该很稀罕、很稀罕了好不好?!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宅女”,轻易不出门、不家访的人,我说好吧,去坐半小时就走,结果是聊了好几个小时……
我刚从德国汉堡回到广州那两年,曾经得了很严重的“失语症”,无论与人面对面交谈,还是打电话,都会忽然间语塞、结巴,词不达意,紧张得脸发红,有时在电话中失语达一分钟之久,才可以憋出第二句话来,往往急得泪眼已婆娑,偏偏却是缺失了一句汉语的修辞和表达;看报纸或看电视新闻也有类似的障碍,好像忽然间什么都变得陌生起来…曾经,老爹和老妈都以为我生了“怪病”,为此忧心忡忡,那些日子,我拒绝故事和回忆,也特别畏惧社交,远离了一切文学圈子,甚至去趟超市都感到羞怯……异乡和故乡如同幻影如同错觉,我同时怀疑过它们的真实存在。有时觉得独在异乡为异客,也好过身在故乡为异客,但也许最好的慰藉和解脱方法是,只把故乡作异乡,象异乡人一样重新去热爱。任教于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刘慧儒老师,是中国最早一批赴德留学生,说起故乡的话题时,他曾经一言以蔽之:故乡,并不存在。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我更加倚赖与凤莲的这种真心无饰的交往,我看重凤莲散文中的真实、真诚与真性情。要从诗歌和小说中看出“文如其人”,要求“文如其人”,这是一种妄想,也是一种没有文学常识的苛刻;然而,散文的内涵和属性决定了它有一种“真实”的品质,与人间的气场最为相通,甚至比报告文学更为讲究“真实可信”,从文字的情绪中更容易触摸到写作者心灵的温度。
世上除了金银珠宝,很多物质都带有闪闪发光的功能,比如能够把人刺痛流血的碎玻璃,靠近时寒气逼人,而远观时竟然也具有非同小可的动人光泽。在这个复杂无间的世态中,在人与文字的身体表里,都可能有意无意地镶嵌着人性的“碎玻璃”,阅读者感到受伤,也是常有的事。然而,与梁凤莲接近,与她的文字相亲,我却是放心和安然,这也许是一种熟稔,也许仅仅是直觉,凤莲的身上,一定也有我所未见识到的棱角和锋芒,我所未感知到的柔媚与风流,但她的身上,我知道,她已经拔除了所有的“碎玻璃”,她是平常心的,真诚的,温暖的,包容的,当然,她也是倔强的,不甘平庸的,不辞艰难的。她有严重的腰椎和颈椎问题,经常疼痛发作,但绝没有一天耽误写作,她有相亲相爱的丈夫与儿子,有安闲生活的条件,却也从未有一天放弃过理想和追求。
梁凤莲将她的广州情绪托付给那些绵绵密密的文字,像岭南三月雨季淅淅沥沥落个不停的细雨,谜一般丝一样的细雨,让人喘不过气,也无法轻浮,只能慢慢地沉浸和感悟。她的文字中有尘世的忧郁和哀愁,有灵魂的无告与挣扎,有知识女性的自尊与矜持,有天真,有热梦,有冰凉的琥珀,也有狂野的鲸,却没有飞扬跋扈的矫情和伪装,也不见什么怨念、醋意与敌视,凤莲就是凤莲,她就是水中的一朵莲,高挑秀丽,有着自己的姿态和坚守,美得那样茁壮坚强;但她也是本色的,是柔软的,是一个性情温良恭俭的广州本土淑女,是一个也会在风雨中摇曳和哭泣的女性……她在《时间之外》所投注的真实无虚的爱与情感,那种生于斯、长于斯、血浓于水的故园情结,她对广州所表达的感恩和感动――“我的内心与状态都是这座城市的氛围气场所孕育所赐予的”,因为有辽阔也有细腻,有见识更有情怀,有涓涓溪流奔赴大海的无悔同执著、勇气与承担,因而构筑了一道独立的绰约的风景线;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天地间,她不卑不亢,郁郁葱葱,你一定看见了她的存在。这本书由“那些广州”、 “那些影像物事”、“那些异乡”交响成章,那些有着执迷不悟的痛感和痴情、那些渗透着温热而潮湿的广州情绪的文字,成为了一个文学广州女性最有说服力的代言。
2016- 3- 19 广州花地湾
陈惠如,笔名陈娃,生于广东。毕业于大学英语系,曾留学德国汉堡和美国乔治城。已出版有诗集《初》、散文集《纯情岁月》《真正的爱情是单相思》、短篇小说集《我是一只梦游的青鸟》,长篇小说《汉堡鸡尾酒》、长篇童话《想变人的小猴子》等,旅居德国多年,现居广州,自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