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标题
内容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广东作家五人谈
更新时间:2017-03-23 作者:曾楚桥、陈卫华等 来源:作品文学月刊

曾楚桥:写作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活着的理由
老实说,我很后悔选择了写作。这苦逼、无趣加无米的活计,我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呢?更奇怪的是,我为何至今还执迷不悟呢?文学真的能安妥我动荡不止的灵魂吗?我认真审视自己,难道我竟是传说中的偏执狂?或者有纯洁癖好的人?但我从来不曾以单纯、善良自居,总觉得自己体内藏着不为人所知的黑,事实上,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这黑会在什么时候突然蹦出来,我害怕它在我无法控制时伤害了别人。我貌似强大的只是躯壳,一个老丑的躯壳,实质内心是怯弱的,也是不可捉摸的。人性的复杂,我在不断地自我审视时,一点一点地体会到了。
一个人如果在过了将近三十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仍然还能淡定地谈理想,谈风花雪月,谈国家大事,萨得和爱国,那我可真的要封他一个圣人的称号了。也许生活中还真的有这种令人景仰的圣人。显然易见,我不是那种人。我做不到如此淡定。所以我只能一败涂地的活着,在尊严扫地之后活着。然而,这世界的变化,我是看到了。那么我看到了什么?我能做些什么?我无力的笔能为弱者提供些什么?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一句话,我得给自己一点活着的理由。
是的,要找到活着的理由。所以我还在写。仅仅是为自己找一个活着的理由。这话透着对世界的厌倦与极度不満。在过了愤青之年,再一次愤青起来,似乎不是好兆头。于是便有了这篇《鲸落》。
在写《鲸落》前半年时间,我一个字没写。期间,好友闫永群因病离世。他在重病中修改他的小说《一个平民的新闻发布会》时,曾和我说过,我们这一代打工人,马上就要被历史遗忘了。那些曾经受过的侮辱也将被历史遮蔽。我即便死了,也不瞑目。
我是在他逝世后,才慢慢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是的,死不瞑目,可能是他对世界最后的看法了。我内心的嘈杂,可想而知。多年来,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突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鲸落》中的罗大春就是好友闫永群,我在文后也题上了献给他。事实上,罗大春也是我自己。在完成初稿时,我没头没脑地大哭了一场。很多年来,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有感动过自己。这一次,算是有点例外了。其实也说不上是感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哭什么。还是那句,我哭的是我自己。在自伤自怜之后,擦干脸上的眼泪,于是就庆幸自己还活在这个一团糟糕的尘世。
活着就意味着一切。不管你千亿身家,还是贫困拾狗屎,都是两手空空的来,最后还是两手空空的走。金银珠宝带不走,狗屎也带不走。当所有的一切指向虚无时,我得为活着找到一个可疑而且虚妄的理由,聊以度日。仅此而已。
曾楚桥,男。广东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六届网络作家班学员、广东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作品刊于《作品》 《收获》 《中国作家》等,部分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观生》和《幸福咒》。

陈卫华:落魄,是生活的真实
小说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吁出一口气,然后加上一行,“2015年5月于无比落魄中”。
当时我有多落魄呢?公司濒临倒闭,身体多种疾病同时在吃四种药,儿子中考因资料不符无法上公立高中,老婆因病住院。坏消息还在来,专卖店也开始亏了,公司年检无法通过,连好好的打印机也说坏就坏了。还有一个建立在我痛苦之上的好消息是,前两年为解决公司资金不足卖掉的一套房两年涨了四百多万。
巨大的身心压力,让我经常半夜失眠,感慨人生。有一天突然就有种强烈的冲动,我要写点东西,是该写点东西了,停笔二十年了。
我用二十天写完小说初稿,晚上有时写到凌晨。尽管累,但总比失眠强。况且时间也不等我了,老婆虽然出院,但不能出门,我要去居委会核对资料,去街道打证明,甚至准备不行就干脆回老家一趟作揖下跪都成,为儿子能读上公立高中做最后努力。公司年检也要重新去工商局、国税查询问题所在,一步一步解决积压问题。毕竟,这比写小说事大多了。
就这样拖着落魄的身躯,又上路了。
有文友说小说中夏风很落魄,灰色了点。其实夏风算好的了,现实中比他更困窘的人比比皆是。在深圳打拼过的人都知道,无论打工还是做老板,这座城市给人的压力都非常大,每天有人负债绝望,每天有人卷铺盖折戟北上,尤其这几年实体经济萎靡和高房价,更破灭了无数人的深圳梦。现实生活本来如此,所以才会有文中真实的夏风。之所以说夏风还算好的,是小说毕竟要给人一点前行的温暖,所以夏风后来遇上了一位好老板薛素萍,让他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而现实中多少人还在风雨中呐喊,在泪光中迷茫,不一样要怀揣勇气生活下去吗?
前几月,在粤老乡年会,好几位老乡喝得酩酊大醉,有哭的有流泪的,丑态毕现。这事其实年年都有。有一位老乡五年没回家了,他说来深圳十七年了,现在仍无房无钱无老婆,典型“三无”,内地教书的工作也辞了,还怎么回?一位说,七十万的时候我没买,一百五十万的时候我没买,四百万的时候我拿什么买?大家都知道他说什么,但没一个人说“房”字。有人说,让他们醉吧,总不能压在心里不让他们发泄一回。老乡年会,终成了落魄人不用伪装的临时皈依地。
小说可以给人前行的温暖,但摆脱不了生活的真实,过多的心灵鸡汤无助于人成长,只增加肥胖。
陈卫华,1967年生,江西铅山县人。1991年开始在江西日报、中国商报、星火等刊发表小说散文。1993年辞职来深圳打工,从事过行政经理、业务员、业务经理、广告策划、副总等多种工作。1997年创办公司,几度沉浮。1998年获深圳华侨城保龄球馆广告语征集一等奖。2015年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有发表及获奖。现居深圳福田。

阿微木依萝:复活那条鱼
我想在屋里刨一个大坑,从地下五十米的地方取水,让坑道逐渐长出青苔,看上去差不多像一口老井。得瞒住所有人。可是这儿昼夜都有人通行,我的门对着巷子口。
这是无意义的事。
我想在对门栽一棵黄桷树。是我家乡那所县城的黄桷树的样子。可这里堵满了新的旧的房屋。我不是房子的主人。我仅仅获得一小块短暂的立锥之地,需要每月缴付租金来保障我可以继续当一名合格的旅客。
这是无意义的事。
我的楼上夜间有人偷偷丢垃圾。我住在底楼。沉重的响声砸在窗口外,有时也从窗口上方的顶棚落下来。于是,我准备开窗偷看具体是谁干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如果幸运地捉住了,就要告诉他,我们这个片区的人的整体素质全都被他拉低了,他是罪魁祸首,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话我可以原谅;如果不愿意,或者更加不幸,他会冲下来打我一顿。可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没有开窗……不,也许开了,或者不是我而是别的什么人。反正等我睡醒一觉,月光就像刀片一样割住我的半扇窗门。他们将我的平板电脑偷走了。
不值一提,这也是无意义的事。
我依然坚持说爱世上的一切要从爱一条陋巷开始。爱这儿的每一个人。包括偷走我东西的人也爱。他们白天从我门口的巷子里出去,在马路边摆上破三轮,上面挂一块牌子:收旧家具。收旧衣服。搬家。拉货。修家电。疏通管道。他们仿佛会干世上所有的活。脏活、累活、大活小活。也说笑话。也抽烟喝酒熬夜。
可这些也是无意义的事。现在我紧迫地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时间过了很久。我在这片地方快要耗光了青春。
如果我要去摘一个众人仅有的月亮会成为公敌。可是我必须这么干。这样才能把我和他们区分出来。
我便默默地在这个既不是故乡也不是长久居住地开始了一系列的谋划。然而,我的野心有多大失败就有多大。我早就预知了。很多人也这样过完了他们的一生。可我不在乎。如果我一直保持着独自享有一轮月亮的理想,我就会一直不在乎。但我长期做梦,有时梦见自己发了大财醒来却还是穷光蛋。就算这种心境根本不能做成什么,我也要坚持。很多事情在我脑海里飞。我必须记下来。我要告诉他们某种力量的存在。这样才能把我和他们区分出来。
我不想躲在房间里写东西了,而是想跑出去,到哪儿随便画点东西,比如画一条岸上的鱼——对,是岸上不是水里,一目了然,人们看了不需要思考就知道它活着但其实已经死了很长时间。这时候,我就要证明自己留住了什么,比如光阴,或者干脆复活那条鱼。我会试着在众人面前给这条鱼一个完整的太阳和月亮,还有一大片海水——创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对,不是那条陋巷的常态,是陋巷的反面。我要证明某种力量的存在。这样才能把我和他们区分出来。
可是毫无意义。我什么也干不了。野心有多大失败就有多大。我已经预知。很多人也清楚。
事情并没有结束。我感到有了很多同伴,蚂蚁般的举着一束光。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吧。他们起初也只想挖一口古井,在对门栽一棵树,爱陋巷中的每一个人。但最后他们全都入魔般的只干一件事:走出门,到陋巷之外,复活那条鱼。
这是无意义的事。蚂蚁般举起的那一束光,不太像一轮月亮。但谁知道呢。
阿微木依萝,彝族,1982年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初中肄业。自由撰稿。现居东莞市。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2011年6月开始文学创作。2012年发表作品。写小说和散文。发表作品多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一部。获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第五届东莞荷花文学散文奖。第三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优秀奖。第二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大沥杯”小说奖。

吴向东:用历史的目光凝望历史
小说《最后一道光亮》,虽说写得是两个老工人的故事,但我更希望它的读者是中青年人。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祖辈父辈,或者是他们在公交或地铁上遇到的某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我出生在武汉一个工业重镇。那里原本是蒿草丛生的荒芜丘陵。五十年代,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和学生汇聚于此。他们衣衫褴褛,忍饥挨饿,脚丫靠脚丫地睡在竹篷里,硬是在这片荒芜的丘陵上,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制造出新中国海军的鱼雷发射管。
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我家的房子,是由红砖砌成的平房,那里一直是父亲班组兄弟聚集的场所。大家抽着劣质的香烟,喝着几分钱一勺的白酒,骂美帝,咒苏修,研究技术革新方案,当然有时也会聊女人。
可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忽地相互之间成了仇人,分成了两个阵营,佩戴着各自组织的标志。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拿着长矛上街。那长矛是用他们共同炼出的钢铁打造。
他们曾是能过命的阶级兄弟,当他们拿起手中的矛刺向对方时,依然拥有共同的理想。可这理想没能阻止他们成为仇人,却让他们的矛尖放着更锋利的寒光。我想历史并不是第一次演绎这样的悲剧,不幸的是我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旁观者和见证人。
我一直想写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为那场血色黄昏后的搏杀,更为他们今天坎坷的命运。那场历史大剧早已谢幕,历史赋予他们角色也悄然褪去。而当新的历史帷幕拉开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必然沦为配角,被忘却甚至被唾骂。可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他们也曾创造出和他们儿孙们一样的辉煌。
写这篇小说时,我想起了大兴安岭的林场工人。他们激情勃发的青春,正被他们用汗水养育的后人,放在键盘上肆意地拷问。他们过去以伐木工人的身份为骄,以为祖国提供栋梁之材为傲。可如今有人却说,那些在铿锵的号子中倒下的原始林木是他们的原罪。就如同那一排排我们曾经无限赞美过的,冒着滚滚浓烟的炼钢炉的烟囱。
如今,风烛残年的他们大多又走到一起。胜利者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失败者也消隐了失败后的落寞。他们依稀尚存的理想,让他们面对当今变幻莫测的世界有了共同的困惑,也有了更多相同的情感。工业重镇里年轻人越来越少,而留下的却是他们耳鬓厮磨之间的懊悔和对往日激情的回忆。望着他们渐渐衰老的容颜,我时常会对自己发问:一群有着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兄弟如何后来会盾矛相抵。
我相信:历史只能用凝望而切忌不可轻佻的回眸。
吴向东,湖北大学物理系毕业。曾获全国孙犁散文一等奖;广东省大沥杯有为小说奖;有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发表于《十月》《花城》 《小说月报》 (原创版) 《清明》 《芙蓉》等中文核心期刊物。

段作文:那些被历史巨轮碾压的生灵
面对这个时代,你可能觉得很好,也可能觉得不那么好,就看你处于何种角度站怎么去看去想去感受。
这些年,我所遭遇的人事,大都是来自底层的呻吟与妥协,偶有抗争,也多以失败收场。这些时代的弃儿,包括我自己,既有客观因素,也有自身因素。这个小说就写了这么一群人,他们的悲喜,看似可期的结局,说不定在哪儿就小说的原标题叫《挖砂》,写到一万字左右时,看起来像个不错的短篇了。同事兼室友楚桥兄看过之后,觉得轻了点,不够透彻,建议弄成中篇。
从短篇到中篇,无论语言、布局、故事还是格调,都得打乱,从头来过。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却也有种莫名的快感。
初稿三万五千字,一气呵成之后,恰好在一次文学活动上幸遇走走老师,我非常诚恳地向她请教。看完稿子,她现场给了一些专业方面的建议,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定帮助。
小说改了三遍,边改边跟楚桥兄就一些细节的真实性进行讨论。待成稿时,它已被砍至两万七千多字。从构思到投稿,历经三个月,那些日子几乎天天都在捉摸这个小说。在决定寄出去时,我又把打印稿给其他同事看,想听听普通读者的意见。这几位同事有一个喜欢看网络小说,他说能一口气看完,我就高兴了,说明还是有相当可读性的。另两位同事是深圳本地人,他们用家乡话反复说着“挖”“砂”,让我对老人家的言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小说究竟说了什么,想说什么,这是作者的事。能读到什么,感知到什么,想到什么,那是读者的事,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等它刊登出来,面对白纸黑字,认认真真读一遍,再读一遍,你就明白这《台风吹过砂沥街》究竟是啥味道了。那台风究竟有多猛,砂沥街究竟是条什么街,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大家就好好去品《作品》里的作品吧。
我在广东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这是第一次在《作品》亮相,一发就是个中篇,还刚好碰到千字500元的稿费,确实令人惊喜。写了这么多年,我是一个发表量相对较少的作者,每一次发表都令人兴奋,大刊物高稿酬兴奋就多一点,所谓的小刊物低稿酬兴奋可能相对小一点。但无论怎么讲,一个稿子能发出来,能有些收入,都是好事,都是肯定,终归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在这个物质与精神倒置的社会,写作作为一种爱好、心性或者乐趣,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在历史巨轮的碾压下,为那些弱小的生灵,为自己,写出痛感,写出性情,写出真诚,我想,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值得去做的。
记忆中这是第二次写创作谈。作品写成后,人物、故事、命运就已经属于作品了,在此,应刊物要求,我简单说说写作过程和感受。我会按自己的路子写下去的,坚持一些,放弃一些,然后进步一点点。
段作文 ,四川广安人,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长江文艺》《四川文学》 《特区文学》等。曾获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第五届“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佳作奖”、第三届深圳 “睦邻文学”年度大奖、第二届“两岸三地短小说大赛”提名奖等,广东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深圳沙井街道文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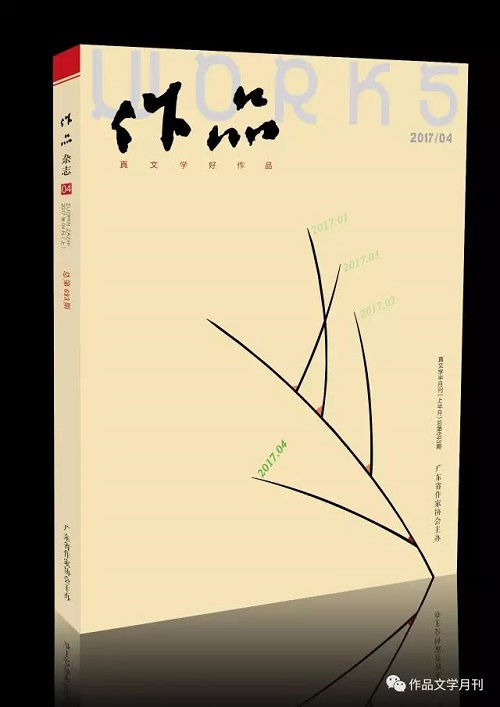
《作品》2017年第4期主要目录
视 点
广东文学的一手好牌
记 录 时代镜像
小世界/海男
虚 构 叙事中国
鲸落/曾楚桥
回家/陈卫华
鱼在岸/阿微木依萝
最后一道光/吴向东
台风吹过砂沥街/段作文
发 现 洞幽烛远
刺客尼古拉耶夫身上的四张牌/王族
推 手 90后推90后(本栏目与《文艺报》联办)
最后一夜/丁颜(女)
囚徒困境/丁奇高(男)
手 稿
我们曾经小说过(外一篇)/汪政
汉 诗
长诗
长沙/雷武铃
短制
草原歌者/郑靖山
女人和她的马(组诗)/远心 评/樵夫
民间诗刊档案(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联办)
《赶路诗刊》/任意好 张建新 等
“典型”立场论——赶路精神与当前汉语诗歌
尊严之我见/任意好
品 读
封二/黄灯 吴佳骏 封三 /李衔夏 陈纸
